在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美学体系与生态美学体系过程中,我们首先要面对的就是黑格尔的“美学之问”,即“中国到底有没有自己的美学”与“有没有自己的艺术”,当然也包括有没有自己的生态美学。而“生生美学”就是对于黑格尔“美学之问”的一种有力回应。
黑格尔在其著名的《美学》一书中认为,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艺术是一种象征型艺术,是“艺术前的艺术”,是“艺术的准备阶段”。他在《历史哲学·中国篇》中更加明确地表示 “在美的艺术方面,理想艺术在中国是不可能昌盛的”。“精神的朝霞升起于东方,但是精神只存在于西方。”新黑格尔主义者鲍桑葵则认为,近代中国和日本的东方艺术“还没有达到上升为思辨理论的地步”。这一看法几乎成为西方学术界的定见。2001年德里达访问上海时也曾说“中国没有哲学,只有思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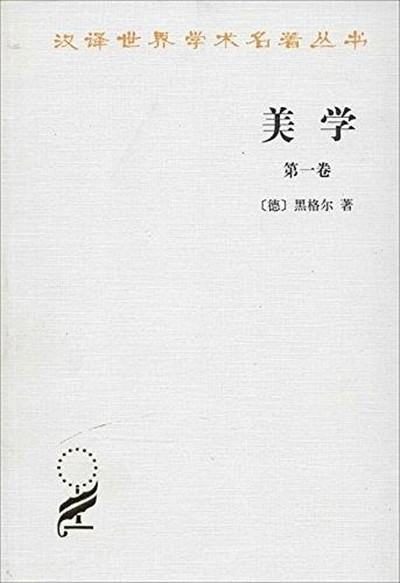
总之,在很多西方哲学家看来,中国没有真正的哲学,也没有真正的艺术,中国艺术没有上升到理性的思辨的高度。这就是所谓的黑格尔“美学之问”,是摆在我国美学建设乃至生态美学建设面前必须要回应的问题。
20世纪初期迄今的百余年来,从王国维开始,前辈学者怀抱着强烈的民族文化复兴愿望,一直为在中西比较交流中创建中国的新美学不懈努力。方东美在1976年指出,“我们优美的青年人具此高贵的民族秉性”,并提出“让现代青年们自信有立国的力量,民族有不拔的根基”。这就是这些前辈学者创立“生生美学”的出发点。其实,中华民族所有的艺术家都在不懈地追求中国的美学与艺术元素。电影人李安就曾说:“中国的历史里不缺少戏剧,不缺少美感,故事更是非常的丰富,我们应该要发展一套能影响世界的电影语汇,给世界电影市场注入新的活力。”所以,中国传统文化中到底有没有自己的美学,这是所有艺术工作者首先需要思考并回答的问题。
我们认为,“生生美学”就是中国古代的美学形态。“生生”来自《周易》“易传”之“生生之谓易也”,“天地之大德曰生”,但其渊源却更加久远。甲骨文之“生”字,许慎解为“进也,象草木生土上”。《尚书》《论语》《诗经》《道德经》等经典均有对“生”与“生生”的论述。由此可见,“生”与生命、生存密切相关,属于中国古代文化的核心范畴。儒家有“爱生”,道家有“养生”,墨家有“利生”,佛家有“护生”;《周易》“泰卦”描述“天人相合”的“泰象”。所谓“天地交而万物生也”,即风调雨顺,万物繁茂,五谷丰登之象。这些都是从不同侧面对“生”所进行的阐发。这就是中国古代人心中的“美”,完全与生态美学相符。只是这种“生生美学”指向一种价值之美与交融之美,而非西方古代的实体认识之美与区分之美;中西美学之间乃类型之别,而非有无之分,“类型说”与“线型说”是中西文化比较不同价值立场的表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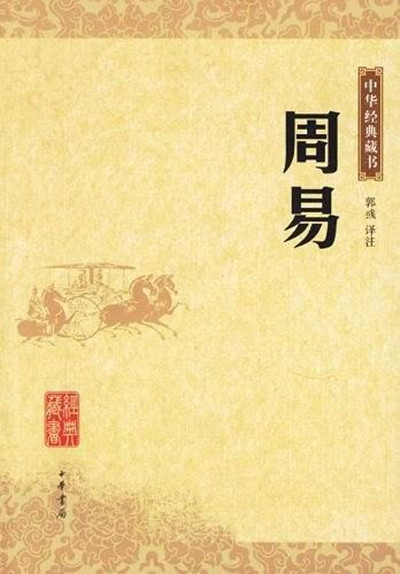
其次是“生生美学”之异于西方的特殊审美原则。“生生美学”是一种东方特有的生命美学。方东美曾明确指出,“一切艺术都是从体贴生命之伟大处得来,我认为这是所有中国美学的基本原则”。所谓“生”包含育种、开物、创进、变通与绵延等义,“故‘易’重言之曰生生”,即“生命的创生”。“生命的创生”是一个过程,也是一种价值,而审美作为对它的“体贴”当然也是一个生命的过程,是一种价值的实现。这种对于生命伟大处的体贴就是中国的生态美学。
再次是要回答“中国古代美学有没有理性”这一问题。黑格尔认为中国古代美学与艺术缺乏理性,事实是中国古代没有西方的工具理性,也没有几何类的理性,却有着极为丰富的道德理性。作为“生生美学”源头的《周易》就使“生生”包含丰富的道德理性,如“天地之大德曰生”“元亨利贞四德”“与天地合其德”等。《乐记》也提出著名的“乐通伦理”,其后,“生生美学”又进一步包含了“仁学”等重要内容,成为儒家道德理性的重要内容。
此外,黑格尔还认为,中国古代“不承认本来只存在于主体内心的道德性”。这也是一种误解。中国古代所谓“德”虽属国家提倡的范畴,却也是个人修养的“功夫”。中国古代强调“修身、养性、正心、治国、平天下”,将“修身养性”提到很高的位置,是君子成长的必要过程。因此并不能说这种道德性缺乏“主体内心”。
其四是要回答中国古代美学的逻辑性问题。黑格尔与鲍桑葵认为中国古代艺术没有上升到理性、逻辑性高度,但实际上中国古代艺术与审美并不局限于“写实”的理性逻辑,而是侧重特有的“意境”逻辑,“言在于此,意在于彼”,包含丰富的审美理想。诸如庄子所言“得意而忘言”、《易传》所言“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司空图所言“象外之象,景外之景”等皆是关于这种审美理想的表述。这也就是说,早在公元前,中国美学就已经有意识地由看得见的追寻背后看不见的,由在场的追寻不在场的。所谓“一阴一阳之谓道也”,从阴阳相生追寻其背后更深的“道”,这就是中国生态美学独特的意境逻辑。

中外美学家:鲍桑葵(左)、庄子(右)
其五是要回答中国古代美学特殊的形态问题。庄子在《知北游》中言道:“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圣人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这里阐明了中国传统“生生之美”渗透于天地生命的变化与创造之中,是深植于“道”之“本根”,因此具有本体性。“生生美学”认为,凡是有生命创造之处都有美的存在,天地乃生命之源,“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因此,中国古代常常在没有“美”的地方发现美,所谓生生之为美也,生命的创生即是美。同时,“生生美学”也是一种交融性美学,真善美是交融的,礼乐刑政也是交融的,很难加以剥离,也很难言说。生生美学的生命本体性与交融性是其与西方古代美学之实体性与区分性的重要区别。
其六是中国古代美学史的特性问题。黑格尔认为古代中国没有美学的历史,但其实中国“生生美学”的历史与西方美学史有着明显差别。西方美学史主要呈现在美学家的论著之中,而中国“生生美学”则主要呈现于各种艺术形态及其理论之中。中国五千年艺术呈现出辉煌而闪耀的美的历史。我们可以粗略地看看这样一部辉煌的历史:先秦之乐及其“礼乐教化”;两汉之书法及其“生命节奏”;魏晋之画及其“气韵生动”;唐代之诗及其“意境之说”;宋代之词及其“婉约缠绵”;金元戏曲及其“歌舞人生”;明清园林之“因借体宜”与小说之“传奇志怪”,等等。这既是实际的“生生美学”的呈现,也是一种具有历史深度的理论发展历程。中国的“生生美学”始终以其独特的光彩而闪耀于世界。
从黑格尔19世纪前期提出关于中国的“美学之问”到21世纪的今天,时代发生了巨大变化。如果在工业革命时期,作为前现代的中国“生生美学”不能被西方接受;那么在后现代的历史条件下,在反思与超越的氛围中,中国的“生生美学”与西方后现代美学却有了更多的共同语言。我们更多的是看到欧陆现象学与中国古代道家“心斋”“坐忘”之相通;看到海德格尔对于老子思想的吸收;看到英美环境美学对于传统艺术美学区分性的反思,提出人与自然环境的“融入性”“参与美学”等概念,以及对于生命之美与“自然全美”的强调,等等。总之,东西方在后现代的相遇,为回答黑格尔的“美学之问”提供了重要契机。

黑格尔
在新时代,尽管“生生美学”所凭借的传统艺术仍具有昂扬的生命力,但其理论形态基本上还停留在前现代模式,本身也缺乏一定的系统性。因此,我们必须对其进行创造性改造,例如为其补充某些科技理性的元素,使之更具理论的自洽性与时代性。使“生生美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到创新性发展。总之,我们仍然需要继续艰苦努力不断创新,唯有如此,才能讲好中国“生生美学”的故事。
(作者:曾繁仁,山东大学uedbet全球体育美学研究中心)
延伸阅读:

中国uedbet全球体育uedbet让所有玩家提款网

“中国uedbet全球体育uedbet让所有玩家提款”微信公号

“中国uedbet全球体育uedbet让所有玩家提款”视频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