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六组关系
探讨艺术学中国学派问题,首先需要做一个区分。区分什么?区分两个系列的关系:一个系列是艺术门类流派和艺术门类学派的关系,另一个系列是艺术流派与艺术门类流派的关系。不过,全面地看,这里实际上涉及至少六组关系:

第一,在门类艺术层面或上横轴上,需要区分艺术门类流派与艺术门类学派的关系。前者是指有独特艺术风格的门类艺术家共同体状况,后者是指有独特艺术主张的门类艺术研究共同体状况,也就是门类艺术创作共同体与门类艺术研究共同体的区分。
第二,在艺术或一般艺术层面或下横轴上,需要区分艺术流派与艺术学派的关系。前者是指多个艺术门类之间有共通艺术风格的艺术家共同体状况,后者是指多个艺术门类之间有共通艺术主张的艺术研究家共同体状况,也就是艺术家共同体与艺术研究家共同体的区分。
第三,在流派层面或左边纵轴上,需要区分艺术门类流派与艺术流派的关系。这就是各个艺术门类自己的艺术家共同体与多个艺术门类之间的艺术家共同体的关系,属于特殊流派与一般流派的区分。
第四,在学派层面或右纵轴上,需要区分艺术门类学派与艺术学派的关系。这就是各个艺术门类中的艺术研究家共同体与多个艺术门类之间的艺术研究家共同体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区分特殊学派与一般学派。
第五,有时候,各个艺术门类流派与艺术学派之间也会发生斜线上的联系。这意味着区分门类艺术家共同体与艺术研究家共同体之间的关系,前者往往成为后者的研究对象。
第六,同样,艺术门类学派与艺术流派之间也会发生斜线上的联系。这就是艺术门类研究家共同体要考虑一般艺术流派问题本身及其在艺术门类中的存在状况。
这样,两条横线和两条纵线上的关系,再加上两条斜线上的关系,共同构成六组关系,都需要做出区分,并且看到它们之间的复杂联系。这里要细说每一组关系的具体情形,可能办不到,因为时间有限。但是,不妨重点说说第一组关系。刚才听得比较多的,主要还是艺术门类流派,如音乐有乐派、电影有影派、戏剧有戏派、绘画有画派等。这比较容易理解,就是分别指音乐家共同体、电影家共同体、戏剧家共同体和美术家共同体。但是,如果是谈论某某音乐学派、某某电影学派、某某戏剧学派或某某画派,也即艺术门类学派,那就需要追问它们的“学”究竟体现在哪里?也就是分别需要音乐研究家共同体、电影研究家共同体、戏剧研究家共同体或美术研究家共同体能够站出来,才能够回答。这也就是需要这些门类艺术研究家切实顶起这顶“学”帽来。当艺术门类流派更多地由门类艺术家去支撑之时,门类艺术学派则更多地需要门类艺术研究家去支撑。他们的分工和贡献各有不同,各得其所。
同时,我想还需指出的是,门类艺术学派除了“学”的支撑以外,同时也需要门类艺术创作及其成果即作品去支撑,也就是门类艺术作品与门类艺术研究一道共同支撑起门类艺术学派。门类艺术作品是基础,在它的基础上生成相应的门类艺术史、门类艺术理论、门类艺术批评等学术成果。假如没有门类作品去支撑,那门类艺术学派就是空的;而假如没有门类艺术研究成果去引领,那门类艺术学派就不成其为“学”乃至“学派”了,很可能只是停留于门类流派的层次上。

二、四个问题
谈论艺术学中国学派,除了上述六组关系以外,需要考虑的问题还有很多。就艺术门类来说,现行中国艺术学学科门类涉及七大门类艺术,按学科顺序排,就有音乐、舞蹈、戏剧、电影、电视艺术、美术和设计七个门类,更别说同样还应该把建筑、书法、摄影等纳入进来(它们现在一般被归入美术学)。同时,如果我们要谈论艺术学中国学派或中国艺术学派,就必须同外国或西方艺术学派做比较,这就涉及艺术学派的知识型或者是知识范式问题。因为,我们一谈艺术学中国学派,肯定就有一个参照系,有一个对象,有一个对话的伙伴,也就是要与外国艺术学派做比较,或者是同它们相对而言。
因此,一旦谈到艺术学中国学派这样一个知识型或知识范式问题,可能涉及至少四个问题需要考虑:
(1)当今世界是否确实存在艺术学派?
(2)什么是艺术学派?
(3)倚靠什么力量去指认艺术学派?
(4) 现在研究艺术学中国学派有什么现实意义?
问题之一:当今世界是否确实存在艺术学派?当今世界上总共存在哪些或者多少艺术学派?而在其中,中国艺术学派有何地位?当前是否是谈艺术学派的时机?如果从共识来看,世界上真的存在艺术学派吗?在英语世界,艺术学到现在也还没有一个专门词语,这是大家都熟悉的,而只能用“艺术研究”之类词组去替代地表达。德国学者玛克斯·德索(Max Dessoir,1867—1947) 于1906 年正式提出“Kunstwissenschaft”,直译为“艺术科学”或“艺术学”。但是这至今没有被英语接纳,至于法语也没有听说接纳。到现在为止的英语国家都还没有“认账”,这是否本身就是一种态度?是不是存在着这种研究各个艺术门类之间的普遍规律的艺术学问?如果有,那它的标志有哪些?如果没有,我们现在来谈,是不是有点时机不对?再说如果有的话,世界上到底有多少艺术学派?我想还是需要去清理的。我们有没有清理过?再说了,假如要谈所有或多个艺术门类都适用的普遍的艺术流派,现在有没有?后现代?后殖民?大数据?人工智能?然后再来谈谈跨门类的普遍性的艺术学派有没有。我这里只是把问题提出来,因为感觉这就是第一层次的问题。世界上到底有多少个艺术学派?在其中我们的地位和作用何在?这是需要共识或大致共识的。假如这样的前提都没有,如何去谈艺术学中国学派?如果说是谈论世界文明古国的艺术,我们恐怕只能谈艺术思想流派和艺术思想体系,而不好去多谈什么“艺术学”或“艺术学科”,因为古代时期还没有这种在现代性以来才逐渐兴起的“艺术学”或“艺术学科”。当然也可以谈,但就比较宽泛和不严格了。那是文明古国时候的事,至少只是一种对现在产生影响的传统或遗产,跟现在没有什么直接的共生关系。我觉得这是需要探讨而又悬而未决的第一个问题或难题。
问题之二:什么是艺术学派?也就是艺术学派的内涵、标准及研究方法等是什么?假设有,真的要谈,至少应当有几方面的基本指标。第一,是否有属于这个学派的一套基本学术概念或学术范畴?第二,与此相连,是否有属于这个学派的一套独特的方法(论)体系?这里是有没有一套,而不只是一个。有没有一整套学术概念或范畴以及方法,是判断艺术学派的最基本的标尺。且不说艺术学派,单就说它的更基本的成熟的艺术学著述,也需要有其在学术概念及方法等领域的独特建树。当年李泽厚的《美的历程》(1981)就至少贡献了两个独特概念,一个是从克莱夫·贝尔(Clive Bell,1881—1964,英国美学家)那里借来的“有意味的形式”说,第二个就是独创的“积淀”说。再有就是在研究方法上形成了艺术观念史研究方法,即是以统一的艺术观念去引领各门类艺术史之间的融通。这本著作,其实称得上是艺术通史或艺术观念史。带着这两个观念,即艺术是有意味的形式以及通过社会实践来积淀,那本来是非实用的、非艺术的青铜饕餮、彩陶等,经过漫长的社会实践积淀后,转化成为有意味的形式—即艺术。可见,一个艺术学派至少需要一整套概念、范畴和方法体系。第三,同样需要联系起来考虑的是,是否有代表性艺术理论家?要有人才做得了学派这个事,形成学术共同体。这里面就包括是否有代表性的论文或著作。第四,是否有标志性艺术作品?或者是否有被重点发掘的艺术品传统?艺术学派的背后,一定要有相应的艺术品来支撑,因为光靠艺术理论或艺术研究还不足以支撑艺术学派。黑格尔需要有具体而又丰厚的艺术作品支撑,例如古埃及艺术、古希腊艺术、现代的浪漫主义艺术等,才能创造出由象征型、古典型和浪漫型三大类型观念组成的艺术理论框架或艺术史概念系统。我觉得要有类似这样一些东西来支撑,包括代表性艺术研究著述和代表性艺术作品,至少满足上述四项条件。如今我们有没有?确实应当认真思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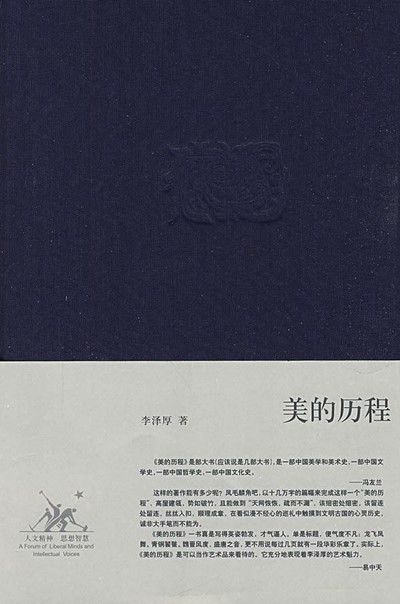
问题之三:倚靠什么力量去指认艺术学派?指认一种艺术学派,同时依赖于两种力量:一种是自我认证,叫自证;还有一种是靠他者来旁证,可称为他证。一个艺术学派的成立,不仅要靠自证,更应靠他证。学派不能仅仅满足于由自我去证明,如公开宣布说我有学派或我们有学派了。光自己说不够,还得由别人来说。一个艺术家说自己是大师,而不是由旁人来说,他好意思吗?权威吗?还是得靠艺术批评家和观众去说。假如我们说有艺术学中国学派,光我们说了还不行,还要旁边的他者说你行才行。为什么人们要照镜子,一定要找一个镜子来对照?就是要靠外在的因素来证明自己。假如我们中国有艺术学中国学派,那就肯定是同其他学派相对而言的,是在一面或多面他者镜子的映照下才成立的,所以他者是一面重要的镜子。只有依靠他者的确证即他证,我们的中国学派才能成其为学派。而假如光靠我们自己说,那就是自说自话,不好,至少不全面。完全是自说自话,就缺乏公信力了。到如今,凭谁来自证和他证艺术学中国学派?想必还有一段不短的路要走。
问题之四:现在研究艺术学中国学派有什么现实意义?也就是现在来谈论艺术学中国学派,对于今天正在进行中的现实的艺术活动—艺术创作、艺术鉴赏和艺术研究等方面,有何现实意义。这一点可能是大家都很明确的:进入新时代以来,人们都在谈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中华文化艺术的繁荣兴盛,同时也需要建立中国艺术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今天确实有这么一个迫切的现实需要,有这么一个特定的时代背景,促使人们来提出和思考艺术学中国学派问题。也就是说,当中国崛起了,特别是经济上或物质上崛起了,需要和希望在文化或精神上也匹配出相应的东西,也即同样实现崛起。这时提出并探讨艺术学中国学派问题,确实具有现实意义。不过,这个问题看起来应当是四个问题中最容易回答的,但同时,也是它们中最不容易说清道明的。因为,经济或物质上的崛起容易找到指标,而文化或精神上的崛起却难以建立指标体系。
前面三个问题确实还不容易说清楚。其中的第一个问题我自己就没有研究。就我自己的有限阅历看,在当今英语世界或西方世界,讨论各个门类自身的规律或特性的学术成果很多,但是把各个门类融通起来探讨的较少。即便是组成像中国艺术研究院这样的学术机构的也很少。斯坦福大学艺术与艺术史系把研究录像、绘画、纪录片等领域的教师放在同一个系,并不是出于统一的普遍的“艺术学”概念,而只是出于一种目前需要,一种不便安排的安排。至于将来是否会接受或接纳“艺术学”概念,有待于观察。不妨想一想,这种不便安排的安排本身,也可能就是一种安排。它说明了什么?说明美国领先高校也已经感到,传统的美术史系单纯研究美术门类已经不够了,需要把不同艺术门类的研究组合或拼贴起来,组成一个系来建构。所以说不定,我们谈论艺术学或艺术学理论学科,中国还是走在前面的,也很有可能是“变轨超车”。
说到底,问题之一、之二和之三都需要花较多时间去研究。研究艺术门类流派比艺术流派要容易,研究艺术门类学派也比研究艺术学派要容易,但都需要有所区别。前不久,有做门类批评的学者就不相信有艺术批评存在,认为只存在门类批评,例如音乐批评、舞蹈批评、戏剧批评、电影批评、电视艺术批评、美术批评、设计批评,不知道什么是艺术批评。门类专家自有他的道理,艺术专家也有其思维逻辑。由此看,研究艺术学中国学派确实是一件很严肃的事,需要相关标准去衡量,依赖于若干证据去支撑,也就是需要回答上面说的这些问题,或者至少在这些问题领域有建树、有推进。这样来思考艺术学中国学派,才是扎实、稳妥的。
说到这里,我还有个或许并非多余的担忧:假如世界上其他国家、特别是文化上领先的国家,一律没有谈论艺术学及艺术学派,而我们自己却在这里单独地大谈特谈它。这样的状况会说明什么?是说明我们已然走在世界艺术学及艺术学派的最前列,还是说明我们依然身处世界艺术学及艺术学派的最后面、外面或边缘?因为,越是被起劲地谈论的东西,或许可能越是恰恰缺少的东西。或者,越想去谈论某种东西,越表明你在那方面缺乏底气。

三、要建艺术学中国学派,先练艺术学中国学说
到这里,我想坦率地说出我的一个观点或建议:要建艺术学中国学派,先练艺术学中国学说。或者更简单:要建中国艺术学派,先练中国艺术学说。学说,我在这里把它理解为学说话。先不提“学派”而先提学说话。先学说情、先学说理、先学说史,还有先学说评,等等,这是不是有可能?先学说话,也就是先把学说(话)做起来,先谈艺术学说。等有朝一日慢慢积累多了,再去说艺术学派。“革命”可以分两步走:先有艺术学说,再有艺术学派。
当然,这两步其实还可以细分成更小因而更多的步子,都是一步一步地来。原来叫大理论、堂皇叙事或大叙事,现在就多做小理论或小叙事。从小理论开始学说,分步走,一步一步地积累。就像建“高峰”,要先建“高原”,而“高峰”这个事不能太急。60年前的1959 年,上海音乐学院学生接到创作任务,要创作一个建国10周年献礼作品,他们面临可以选择的三个题目:第一个是“大炼钢铁”,当时是在“大跃进”的热潮中;第二个是“全民皆兵”,那会儿最火的题目;第三个才是民间爱情传说“梁祝”(也就是现在的“非遗”),当时还算不上热潮。按照这批年轻学生们的直觉,这三个题目的重要性是依次递减的,因而他们对此的创作兴趣也是递减的。但最后,学院领导拍板做“梁祝”,因为它最适合小提琴协奏曲,当然得服从。没想到一举而取得巨大成功,一下子就创作出这么多年来人们还要不断回味和景仰的音乐经典。[1]我问了音乐界的一些专家,如果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音乐方面有经典或有“高峰”的话,那么这个肯定算。这样一下子就创作出60年来的音乐经典或音乐“高峰”,当年的年轻音乐人自己是不可能预想到的。起初不起眼的小题目,居然可以做成大经典。
总之,要建艺术学中国学派,先练艺术学中国学说。一步一步地来,或者分多个步骤走,做多了,一点点积累起来,说不定谁就在这方面有突破。当这样的积累和突破多起来,艺术学中国学派的基本条件就逐个地得到满足了。那时,或许就有他人发自内心地出来指认了,而不必等到我们自己来说了。到那时,当我们自己不说艺术学中国学派时,或许就有了,也就是了。至于目前,恐怕还是少谈学派而多做学说为好。
注释
[1]参见黄旭东:《艺术明珠“梁祝”创作过程真相—协奏曲创作的参与者与知情者访谈实录》,《音乐爱好者》2008年第12期;烁渊:《“梁祝”策划的最新解读》,《决策与信息》1999年第8期。
来源:《艺术学研究》2019年第2期

(作者:王一川,中国文联主席团委员,中国uedbet全球体育uedbet让所有玩家提款家协会副主席,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延伸阅读:

中国uedbet全球体育uedbet让所有玩家提款网

“中国uedbet全球体育uedbet让所有玩家提款”微信公号

“中国uedbet全球体育uedbet让所有玩家提款”视频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