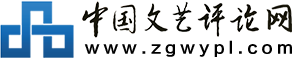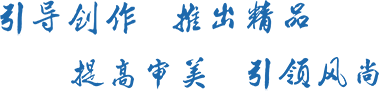“可能世界”与影视剧本体观念的拓展——从国产时空循环剧出发
(第四届网络uedbet全球体育uedbet让所有玩家提款优选汇优秀长评作品,发表于《中国电视》2023年第4期,由作者参选提供)
2022年,剧集《开端》因“无限重启”的时空循环结构、纵横交错的情节线索与高潮迭起的悬疑推理桥段备受瞩目。随后,《一闪一闪亮星星》《超时空大玩家》《救了一万次的你》《天才基本法》《乌云遇皎月》等剧集相继出现,不约而同地采用了时空循环的游戏化设定,成为剧集领域值得关注的现象。国产时空循环剧采用分岔路径情节与化身叙事开启虚构世界的可能形态,并通过循环往复的时空展现了故事世界的丰富性与世界之间的通达关系(AccessibilityRelation),同时,还在时空循环开启的“世界”中植入了与网生代青年群体密切相关的现实议题与现实情境,对接了网生代青年受众的情感结构,获得了较高的收视率与口碑。可能世界叙事学研究“世界”的构筑方式、运作形态及其对创作者、文本与受众的联结作用,为研究国产时空循环剧的叙事机制与空间修辞提供了较强的启发性与阐释力。本文首先梳理可能世界叙事学的理论框架,继而考察国产时空循环剧的叙事机制与空间修辞,最后探讨国产时空循环剧如何对媒介融合时代的剧集本体观念形成拓展。

《开端》海报
一、理论引渡:可能世界叙事学的理论谱系
“世界”是后经典叙事学的重要隐喻,它为文本、创作者与受众搭建出共享的关系网络。可能世界理论穿梭于哲学、逻辑学与文学等多个学科领域。学界普遍认为,可能世界理论源自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他提出:“世界是一切现存事物的整个顺序与集结,存在着无限多的可能的世界。现实世界是实现了的可能世界,是所有世界中的最优选择。”模态逻辑语义学的代表学者克里普克把可能世界界定为整个世界的存在方式、状态或历史的总和。克里普克将可能世界挪用至语义学领域,为模态逻辑建立了完整的语义学理论—可能世界语义学,以表达“必然”“可能”“或许”建立的可能世界的逻辑真值问题。大卫·刘易斯在克里普克的基础上提出“替代性可能世界”(Alternative Possible World)的概念,认为“所有的可能世界都能够被再中心化于它的任何行星之上,因此包含有无穷多个现实世界……我们可以透过心理行为,将另一个世界指认为现实世界,并通过进一步的想象编制出一个围绕该中心的替代性可能世界网络”。刘易斯的论断打破了西方哲学传统中现实与虚构的二元对立,他认为虚构的可能世界与现实世界同样重要、同样完整、同样具有存在的价值。
在叙事学领域,亚里士多德早在《诗学》中就表达了他对“可能发生”之事的重视:“诗人的职责不在于描述已经发生的事,而在于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即根据可然或必然的原则可能发生的事。诗是一种比历史更富哲学性、更严肃的艺术,因为诗倾向于表现具有普遍性的事,而历史却倾向于记录具体事件。”虽然亚里士多德提出的“模仿论”运作于单一世界,并未涉及“可能世界”与多层级的“文本宇宙”,但他肯定了“虚构”与“可能”的合法性地位,为“可能世界”的后续发展奠定了基础。
20世纪以来,可能世界理论逐渐被叙事学吸纳,讨论叙事作品中虚构与真实、内容与话语之间的复杂关系。叙事理论中的“可能世界”也转化为“虚构世界”与“故事世界”这两个概念。“虚构世界”涉及本体论,脱胎于哲学“可能世界”,强调虚构具有和现实对等的主体性地位,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文学理论界与哲学理论界的话语权争夺;“故事世界”涉及认识论,是当代认知叙事学的核心,强调对叙事的阐释核心在于受众的心理框架。两者在很多语境下可以通约。
“可能世界”位于修辞叙事学与认知叙事学的交叉地带,它既涉及作者的修辞策略,又与读者的认知框架息息相关。可能世界叙事学是阐释“可能世界”的叙事理论。在修辞层面,可能世界叙事学旨在阐述虚构世界的编码建构、动态生成与持续扩张。在认知层面,可能世界叙事学旨在表达故事世界的解码重构、心理感知与情感体验。认知叙事学的领军人物戴维·赫尔曼提出“叙事理解就是建构和更新大脑中的认知模式的过程,文中宏观和微观的叙事设计均构成认知策略,是为建构认知模式服务的”。
可能世界叙事学为研究叙事作品中的情节装配、人物设定与世界构架提供了基础。可能世界叙事学的集大成者玛丽-劳尔·瑞恩提出,可能世界理论向文本符号学提出了两个概念:“世界”隐喻用来描述文本所投射的语义域;模态概念用来对构成语义域的客体、状态、时间的各种存在方式进行描述和分类。她进而提出“虚构的再中心化”(Fictional Recentering)概念,为研究“故事世界”的模态关系、叙事进程与叙事机制等问题提供了具有阐释力的理论框架。
文学中的虚构世界通过语言修辞,在语义域投射并被受众认知与唤起;影视剧中的虚拟世界通过视听修辞,在屏幕建构并被受众感知、解码与重构。可能世界叙事学用多元世界框架取代了传统模仿论中的单一世界框架,为叙事艺术的“世界”建构与虚构理论提供了分析基础,也为国产时空循环剧的叙事特征及其多模态可能世界的运作方式提供了阐释思路。
二、叙事机制:岔路情节与化身叙事
在国产时空循环剧风靡之前,时空循环形态的复杂叙事(Complex Narrative)已在电影领域大量出现。在21世纪之前,这类电影的代表作包括《盲打误撞》《滑动门》《罗拉快跑》《一个字头的诞生》《土拨鼠之日》等。21世纪以来,游戏与影视作品之间的借鉴、渗透与互融愈发深入,二者的“联姻”亦促成了吸纳游戏视觉形态与叙事机制的“游戏化电影”(The“Videogame”Film)和吸纳电影视觉形态与游戏机制的电影化游戏(The“Cinematic”Game)的大量出现。⑨《盗梦空间》《源代码》《明日边缘》等影片通过非线性、模块化与数据库叙事等形态构成了“谜题电影”与“心智游戏电影”等类型,体现出游戏与电影在新媒体与新技术语境下的交融互渗。
在可能世界叙事学的视域下,时空循环剧通过“世界”的开启打破了传统影视剧集的透明、线性、闭合与连贯等叙事惯例,充分测试了剧集叙事在表征形态与修辞方式上的种种可能性。
国产时空循环剧采用游戏的逻辑与运作机制来建构剧中的可能世界。这种游戏化叙事主要由“分岔路径情节”(Forking-path Plots, 简称“岔路情节”)与人物的化身叙事组成。岔路情节是由电影理论家大卫·波德维尔依据博尔赫斯的文学作品《小径分岔的花园》(The Garden of Forking Paths)提出的概念。⑩它基于“What If”(假如……会怎样)的因果假设,探索情节在某一意义时刻因分岔导向的多重叙事进程及其可能性结局。分岔路径不仅形成了情节的多重线索,更是在某个意义时刻开启了分岔的可能世界,为“文本宇宙”提供了多重可能。由于多重可能世界由同一个故事展开,因此无论背景故事是否在下次循环后复现,受众都不需额外付出认知努力。
存档与读档(Save/Load)是国产时空循环剧游戏化叙事机制的重要体现。主角依靠存档与读档略过重复情节,跳入情节分岔点开启全新的任务召唤。通过循环往复的存档与读档,主角获取经验,实现成长,破解关卡,抵达结局。如《开端》的主角李诗情和肖鹤云为了阻止公交车爆炸而循环往复地穿梭在公交车与乘客的可能世界中,最终破解了爆炸危机,成功完成游戏任务;《一闪一闪亮星星》的女主角林北星为了拯救男主角张万森,无数次重启回到学生时代,从旧时光中打捞出珍贵的爱情记忆。时空循环剧以同一个故事衍生出多个可能世界,带领受众游历其间,探索世界的架构、逻辑与法则。
“选择”与“解谜”是国产时空循环剧主角的主导行动与贯穿动作。两者如影随形,共同强化了谜题构成的复杂叙事与游戏任务。主角通过“选择”与“解谜”突破关卡,将剧情代入下一个分岔点,开启次级可能世界的大门。每个分岔点作为外在的意义事件,对应着内涵于“选择”与“解谜”的意义时刻。意义时刻意味着在事物的状态中,总有外在形态与内在本质最接近的一刻。这一时刻暗示了过往、当下与未来,比其他时刻更关键、更本质,更具穿透力,因而更重要。⑪意义时刻宣告和凸显了可能世界大门的开启。国产时空循环剧的经典意义时刻包括《开端》公交车上的“梦醒时分”、《一闪一闪亮星星》中删除手机短信的“眩晕之刻”与《天才基本法》回忆之墙的“涂抹公式”。它们的共同特点是:既是“选择”与“解谜”动作出现的节点,又与主角的命运转折紧密相连。随后出现的可能世界往往揭示出主角的背景故事及时空循环的核心目标:在扑朔迷离的时空碎片中打捞过往的记忆,探索亲人与爱人的悲剧真相或弥补过往的遗憾。如在《天才基本法》中,男主角裴之进行时空循环的核心目标便是与女主角林朝夕重聚并使自己的父亲在车祸中幸免于难。无限重启能够通过经验的习得与世界的重生弥补缺陷,虽然消弭了悲剧的深度体验,却替代性地弥补了遗憾,与过去和解,为剧集的现实底色点缀了梦幻色彩。国产时空循环剧的受众也在主角面临“选择”与“解谜”的过程中提升了对复杂叙事的认知与接受经验,在谜题的召唤下获得了参与快感与智性愉悦。
化身叙事是国产时空循环剧游戏化机制的另一重体现。化身是游戏化操控的直接表现形态。在电子游戏中,玩家依靠对游戏角色的操控与游戏世界互动,获得具身性的认知体验,在游戏世界中获得了意识与权力。游戏角色与其说是玩家的操控对象,不如说是玩家的化身,玩家借由该角色在游戏虚拟世界之中沉浸,进而模糊玩家与化身的界限,实现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的连接。⑫在视点呈现方面,化身叙事也是游戏化情节的前置条件。在《天才基本法》中,“草莓世界”的林朝夕不断穿越进入“芝士世界”的自身躯体,进而改变自身、男友与父亲等角色的未来,弥补过往的遗憾,书写了人生的另一种可能。《超时空大玩家》《救了一万次的你》中平凡的主人公也化身成为特殊能力的掌控者。这种为了拯救爱人而不断时空循环的主题使时空循环剧形成了悬疑与爱情类型交织的稳定框架。规律化的情节线索和逻辑化的因果链条共同构成了逻辑自洽与充满想象力的故事世界。国产时空循环剧也在一定程度上彰显出影游融合与想象力美学的特质。
需要注意的是,化身叙事并非时空循环剧的首创,它很早便出现在电影、动漫与游戏等领域。在查理·考夫曼编导的谜题电影《成为约翰·马尔科维奇》之中,观众潜入马尔科维奇的大脑操控其意识;在漫画领域,浦泽直树创作的漫画《20世纪少年》也展现了通过VR游戏潜入“朋友”童年记忆的情境。国产时空循环剧《乌云遇皎月》中男女主角的双视点及其时空循环机制也与漫画《夏日重现》和《只有我不在的街道》具有异曲同工之妙。即便如此,时空循环在过往的国产影视剧集中却不多见。《开端》等国产时空循环剧的集中出现填补了这一领域的空白,刺中了网生代青年受众体验虚拟人生的“幻想神经”,满足了该群体在现实中追逐幻想的诉求。与电影作品不同,剧集具有更长的篇幅展现更为波澜壮阔、绵延起伏的世界图景,这就提供了展现更多“可能世界”的机会。通过人物化身叙事形成的游戏化表达使受众沉浸在剧集所述的“世界”中,“世界”也获得了广阔与丰富的想象和建构。

《一闪一闪亮星星》海报
三、世界建构:空间修辞与人物拓维
“世界”既是经验性术语,又是空间术语,它由文化、习俗、事件、空间和地点所界定。在可能世界的理论视域下,虚构作品建构的故事世界是与现实世界同样具备主体性与合法性地位的可能世界(时空连续体)。虚构作品通过故事世界为作者、文本和受众之间的互动关系搭建起交流系统。在文本层面,叙事活动推动了虚构世界/故事世界建立内部自洽的行为逻辑、运行法则与价值体系。在接受层面,受众沉浸在虚构作品建立的可能世界之中,唤醒了对文本所述世界的认知与认同。国产时空循环剧采用“现实化”的空间修辞逻辑建立其故事世界,保持着与现实世界较高的通达性,并通过对人物要素的强化而照亮故事世界的疆界并描绘其图景。
(一)“现实虚拟”的空间修辞策略
影视剧建构的虚拟世界与受众所在的现实世界的距离,既取决于两者的重叠程度,又取决于受众对虚拟世界的熟悉程度。瑞恩认为“通达关系的数量越多,现实世界与虚构世界的距离便越近”。她进而提出九种通达关系变量,锚定并细分了虚构世界与现实世界的通达性与跨世界同一性。这些通达关系包括“属性的同一性”“存在物清单的同一性”“存在物清单的兼容性”“编年的兼容性”“物理的兼容性”“分类的兼容性”“逻辑的兼容性”“分析的兼容性”“语言的兼容性”。
与文学作品经过语义域投射出的虚构世界不同,影视剧建构的虚拟世界是经过摄影机拍摄而成的“现实的渐近线”。在空间的形态建构上,国产时空循环剧并没有走向魔幻、玄幻或古装奇观类作品的架空历史与幻想空间,而是在现实取景,将现实空间搬演至荧屏,从而形成了“现实虚拟”的空间修辞策略。这种策略主要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首先,在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之间建构高度重叠的通达关系。为了实现虚拟世界的逼真感与现实沉浸感,国产时空循环剧在属性、存在物、物理、分类、逻辑和语言等方面均以现实世界为依照,依靠对现实的逼真再现形成与现实世界稳定的通达关系。《开端》《天才基本法》《一闪一闪亮星星》等国产时空循环剧不约而同地采用了与现实世界相同或相似的法则与运行逻辑。这样不仅能够节省制作成本,带来扑面而来的现实质感与沉浸感,而且避免了为解释故事世界机制而占用情节篇幅。
其次,在虚拟世界中植入现实议题,提升现实质感。瑞恩认为,“指涉世界与它的形象密不可分,对形象的沉思会自动将读者带入它所表征的世界之中”。高考、竞赛、职场等元素与网生代青年受众群体认知框架与生命体验中的“现实”形象重叠,相似的情境使之更容易获得感同身受的认同体验。如上所述,时空循环剧的目标是挽回过往的遗憾,拯救所爱之人。结局往往是最优化的解决方案。《救了一万次的你》和《超时空大玩家》中的主角运用“时空循环”能力与游戏世界中的“声望值”解决了诸多社会问题,不仅与世界中的伙伴建立了关系网络,主角也在过程中实现了个人成长。此外,现实议题还能够形成虚拟世界朝向现实世界的反向跃迁,进而对现实世界产生积极影响。《天才基本法》的流行激发了荧屏外受众的数学热情,剧中的“21点”“孔明棋”等数学游戏与“巴什博弈”“哥尼斯堡七桥问题”等数学问题也成为现实话题,在互联网社交平台上获得了大量讨论,由此实现了知识启迪、价值引领与人生励志等作用,传递了积极正面的观念与情感,体现出时空循环剧的社会服务功能。
再次,通过空间表征,为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提供“界面与接口”。国产时空循环剧虽未刻意呈现拍摄地的真实名称,但深焦之处可供指认的关键场景依然暗示了荧屏世界取自现实世界,从而使剧集所述的故事世界与受众所居的现实世界对接。《一闪一闪亮星星》以厦门的环岛路和老鱼港沙坡尾作为主角林北星与张万森的青春舞台,以中山公园动物园作为成年林北星的职场环境。《开端》以厦门的海沧大桥作为“开端”,将网红咖啡馆“锅炉咖啡”打造为主角李诗情与肖鹤云商量对策的“根据地”。不仅如此,剧中出现的“山海健康步道”等螺旋状的建筑物与偶尔可见的莫比乌斯环(如出现在角色卢笛帽子侧面的图案)也传达出“时空循环”的观念。在空间修辞的策略下,时空循环剧建构的虚拟世界为现实世界增魅,使现实世界笼罩了幻想色彩。受众能够在现实世界中追逐时空循环的浪漫、梦幻与奇观,获得从“时空循环剧”到“都市传说”,再到“城市旅游”的三重审美体验。幻想与现实的交错体验无疑也进一步加强了受众对虚拟世界故事的沉浸、投入与认同。空间表征也使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交相辉映,相互观照。
“现实虚拟”的空间修辞策略使国产时空循环剧呈现出与现实世界若即若离,既有现实质感又有幻想气质的虚拟世界形态。有学者提出:“伴随着‘虚拟现实’技术的发展,大众在消费过程中逐渐形成对‘现实沉浸’的消费诉求。”受众通过沉浸想象与深信不疑,进而投入虚拟世界的怀抱。在故事世界内部,“现实虚拟”通过对现实的高度重叠为受众建立与游戏化叙事匹配的沉浸感;在故事世界之外,它呼应了元宇宙、VR游戏引擎等虚拟现实技术的蓬勃兴起。这种叙事修辞策略独具一格,带来了清新的时代气息。
(二)多元人物的世界疆域拓展
可能世界叙事学的另一个重要理论贡献在于对形式主义与结构主义过度强调叙事功能而忽略人物形象的传统予以修正,重新肯定了叙事人物对世界建构的重要支撑作用。人物不再是构成形式与结构的被动要素,而是能够为虚构文本的可能世界拓展疆域的能动力量。
瑞恩在模态逻辑哲学理论与道勒泽尔的模态类型学分类基础上提出了“虚构的再中心化”(Fictional Recentering)概念并预设了三个模态系统和三个世界:一是现实世界(The Actual World,简称AW):有血有肉的真实作者与真实受众生活的本土系统。二是文本现实世界(Textual Actual World,简称TAW):文本投射出的世界,它位于文本宇宙(Textual Universe,指文本投射出的所有世界的总和)的中心,被文本替代性可能世界(Textual Alternative Possible World,简称TAPW)围绕。三是文本指涉世界(Textual Reference World,简称TRW):既包含文本投射的世界,也包含留有空白、被读者想象填充的一切。将瑞恩的界定转化到影视剧领域,TAW是由影视剧通过屏幕直接呈现的世界样貌,受众通过图像与声音习得TAW,并通过TAW感知TRW—更广袤的世界的存在。瑞恩提出,文本宇宙能够使其内部的任何可能世界“再中心化”,使其位于系统中心来组织模态系统。“虚构再中心化”打破了现实世界中心论的绝对主义立场,提升了虚构世界的重要性与地位。更重要的是,它意味着在文本宇宙的内部,替代性可能世界也具有成为现实世界的可能。在《天才基本法》的初始阶段,“草莓世界”是处于文本宇宙中心的TAW(文本现实世界),“芝士世界”是“草莓世界”的TAPW(替代性可能世界)。而随着故事的发展,两个世界通过博弈、竞争与对抗发展出各自的主体地位,“芝士世界”也通过“再中心化”的方式使自身从“草莓世界”的TAPW发展成为与“草莓世界”平行且独立的TAW。最终,栖居于这两个平行时空中的角色实现了各自的价值,受众也在观剧过程中调整认知与情感逻辑,获得了对《天才基本法》文本宇宙及其可能世界关系网络的完整认知。
从叙事的修辞层面来看,替代性可能世界能够通过“再中心化”,使多元化的角色人物(尤其是配角)获得主体性地位,进而获得作为“主角”的叙事进程展示。《开端》就呈现了芸芸众生的鲜活群像:渴望被家人认可的二次元少年卢笛、师徒情深的张队长和小江警官、出狱后给儿子送西瓜的老马、拖着拉杆箱朝不保夕的老焦……这些群像人物的替代性可能世界通过重启得以建构和“再中心化”,获得了其欲望、困境与突围的叙事进程展示,照亮可能世界的地图疆域,也进而开启了文本宇宙的多重平行时空。
从叙事的认知层面来看,受众借由以往的审美经验和类型预期,对影视剧建构的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进行参照性阅读。在这种观看动力的驱使下,受众“在重建虚构世界时,通过假设文本与现实世界的相似性来填充文本留下的空白”。这也就意味着,受众将自身的审美与认知经验投射在作品中,从多元人物的可能世界中获得对文本宇宙的整体认知。作为建构可能世界的叙事支点,多元人物的作用在国产时空循环剧中得到强化。时空循环也借助影视剧较长的篇幅对多元人物进行了全面展示,进而丰富了世界图景。
多元人物的关系网络在存档/读档的游戏机制下使可能世界之间形成了更为丰富的,跨越时空的通达性与因果关联。某个世界甚至能够为其他世界提供推动关卡与解谜的线索。如在《开端》的第12集中,女主角李诗情询问张队长,假设突然接到陌生人的报警电话,告知公交车上埋藏炸弹,警队是否会选择相信?张队长以“毫不犹豫出警”作为回复。而在时空重启之后,李诗情根据上一次循环中与张队长的“假设推断”,不仅提前发送短信向张队长报警,还为警察争取了时间。最终警察果断出击,在与全车人的配合下保护了无辜乘客,成功塑造出人民警察值得信赖的正面形象。另一处是在二次元少年卢笛作为文本宇宙中心的时空中,主角获得邀请他的“暗号”。在之后的替代性可能世界中,主角凭借这个“暗号”瞬间获得了卢笛的信任与协助。这两个例子别开生面地演绎出可能世界的通达与因果关联。而陌生人之间的惺惺相惜和以命相许,也让该剧散发出热血与感动的味道。《天才基本法》也通过多元人物的选择表达出全剧的核心理念:“芝士世界”并非“草莓世界”的替代品,每个人也都是独一无二、不可替代的;无论身处哪个世界,都应该拥有面对困境的信念与勇气。多元人物通过时空循环产生了“跨世界”关联,国产时空循环剧也实现了视听奇观性与叙事复杂性的协作与平衡。
四、本体拓展:媒介融合时代剧集的游戏
本体观念及特征如果从最普遍的意义上理解电视剧,相对不会引起争议的定义是:电视剧是基于时空与视听的传媒艺术形态。“电视”决定了它的播出渠道(电视荧屏);“剧”显示出它与戏剧的血脉相连。其中,电视荧屏是决定其本体观念的重要物质基础。
电视剧理论的发展史就是剧集本体观念随着时代发展而修正与更迭的历史。电视剧无可避免地受到同时代文化思潮、技术迭代与其他艺术形态的影响,这些因素共同构成其本体观念变化的助因。有学者总结,在电视的发展历程中曾形成过戏剧观(屏幕演剧阶段的戏剧艺术)、电影观(影像艺术与视听艺术)与电视观(具备电视节目共有属性的电视艺术)等本体观念,三者随之形成了电视剧独特的“三位一体”本体观形态。电视剧本体观念的讨论随着20世纪80年代“美学热”形成高峰。之后,随着剧集创作的高度繁荣,电视剧研究经历了由“本体研究”到“文本批评”的研究范式转换。本体研究的讨论被搁置,文本批评日渐成为剧集研究的主流形态。
近年来,媒介融合使传统剧集的产业生态与艺术形态发生了转变。在产业生态方面,互联网流媒体平台、视频网站与各种移动终端的普及改变了剧集的传统生产与传播渠道;在艺术形态方面,电影、游戏与新媒介带来的冲击也使影视剧的内容与形式呈现出多样化的变化趋势。这也就对传统的剧集本体观念带来冲击和挑战。时下,面对产业生态与艺术形态的转变,讨论剧集本体、厘清其内涵与外延,不仅是影视剧艺术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当下中国影视剧产业与行业发展的内在需求。
影视剧的本体观念与特征(是什么)与影视剧的观看终端与场景(在哪看)及观看方式(怎么看)息息相关。在媒介融合的生态下,观剧行为不再需要在阖家团聚的客厅内围绕着电视机展开。各种屏幕(手机屏幕、平板屏幕与电脑屏幕)正在逐渐成为影视剧集的主要观看终端,受众可以凭借其便携性与可操作性在地铁、公交等任何空间观看剧集。同时,借由计算机、平板电脑与手机屏幕的界面操作,受众获得了对剧集时间的操控权力,能够凭借“倍速观看”“逐帧观看”与快进、快退等形式反复观看与检视,这就扭转了传统电视台观剧的线性接受与认知体验,并能使受众攫取更加复杂与精密的碎片化信息。可以说,观看的终端、时空与方式变化都为剧集本体观念与特征的升级提供了契机。
视频网站介入影视剧的生产与流通环节后,“怎么讲故事”(形式)的重要性也逐渐凸显。面对电影、游戏等媒介形态对受众时间的多方位挤占,“前所未见”的形式吸引力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2022年多部国产时空循环剧的“横空出世”便体现了剧集的形式探索。“在新媒体的交流系统中,时间被擦除了,过去、现在、未来变成了互动的关系。”国产时空循环剧体现出新媒体时代的互动时空特征。更重要的是,时空循环的叙事形态彰显了这样一个事实:在网生代青年受众对叙事形式和游戏体验的潜在消费需求下,游戏已深度嵌入剧集的本体层面,使剧集在叙事机制、叙事内容与叙事接受等方面具备了游戏的观念与特征。
首先,在叙事机制方面,时空循环形成的岔路情节与化身叙事本身就是高度游戏化的机制设定。如前文所述,受众与玩家处于同一视点,依靠重启、存档与读档穿梭在故事世界中,展开对任务关卡的反复解谜;循环后既有可能化身进入自身的躯体,亦有可能进入他人的意识,开启全新世界的冒险之旅。创作者也不再囿于剧集生产者与制作者的身份,而在一定意义上获得了游戏设计师的身份与权力。
其次,在叙事内容方面,时空循环剧在人物的职业身份、故事内容与情节桥段等方面植入游戏内容与游戏惯例。《开端》中主角肖鹤云的职业身份被设定为游戏设计师,《超时空大玩家》直接采用“玩家”为剧集命名,其奖励机制、特殊道具与故事桥段也源自游戏的常见内容。《救了一万次的你》的主角想利用时空循环的游戏漏洞购买彩票不劳而获时,彩票却不断被风吹、被雷劈、被车碾压、坠入井底……展现了循环设定的副作用与惩罚。时空循环展现的不同可能世界之间的“超链接”、记忆的改变、擦除等档案材料特征也与曼诺维奇提出“数据库叙事”(Database Narrative)形态不谋而合,充分体现了互联网时代影视剧叙事内容的游戏特征。
再次,在叙事形式方面,时空循环剧通过“现实虚拟”的形态形成游戏化的现实沉浸感。如《一闪一闪亮星星》虽然形成了游戏化的循环穿越,但回到了青春时代的校园现实之中。《救了一万次的你》和《天才基本法》中的虚拟世界也具有和现实世界相同的逻辑架构与现实法则。值得一提的是,为了避免视听奇观对现实沉浸感的破坏,目前只有《超时空大玩家》等剧中采用了少量的游戏视觉拟态与操作界面,大多数时空循环剧走在了游戏视觉奇观展示的《穿越火线》等电竞剧的对立面。这种“现实虚拟”的空间修辞策略与其情感效果所带来的沉浸体验也是游戏沉浸逻辑的有机组成。
最后,在叙事接受方面,时空循环将传统的线性叙事分散、打碎,使之散落在文本宇宙的角落,在游戏化的接受预期下,受众通过收集、挖掘和组装与“文本宇宙”互动,参与“可能世界”的重建,进而获得游戏化的审美体验。同时,技术赋能带来的“倍速观影”与“反复观看”也使受众掌握了“时空循环”与“化身”的“超能力”,能够使受众通过游戏玩家的接受视角获得游戏般的审美体验。
值得留意的是,国产时空循环剧的游戏本体观念早已蕴含于其IP原作本身携带的游戏特质之中。《超时空大玩家》《开端》《乌云遇皎月》均改编自带有游戏元素的网络文学作品,而《救了一万次的你》改编自韩国漫画。IP原作中的核心主题“穿越”和“重生”本身就带有“现实虚拟”的游戏基调,满足了网生代青年受众对“虚拟人生”的情感体验与消费诉求,也为改编奠定了游戏化基础。因此,国产时空循环剧较为自然地结合了原作奠定的游戏叙事机制与“现实虚拟”策略,呈现出游戏美学的特点,凸显了影视剧的游戏本体观念特征。
国产时空循环剧的游戏本体观念还得益于技术赋能与文化创意行业间的跨界交流。腾讯、爱奇艺与优酷等视频网站本身便携带着丰富的互联网与游戏基因。这也就使它们在介入影视创意产业时,更容易促使剧集与游戏在产业、内容与形式机制等方面的有机融合。传统影视剧的线性叙事与电视台的首播制度息息相关。如若呈现过多令观众“烧脑”的信息,很容易流失收视率。与此相反,网络平台为受众提供了反复观看的可能。即时弹幕、网络uedbet让所有玩家提款与网络社群为复杂叙事与碎片化信息的接受与理解提供了信息补充。由此,互联网空间为影视剧游戏化的复杂叙事形态带来了重要支持。此外,电影与游戏行业的跨界创意人才与制作人才流入剧集行业,也为其带来了电影化、游戏化与网络化的创作理念、叙事技巧与视听语言。游戏化的界面、叙事结构与时空设定早已融入电影领域。除岔路情节外,还具有模块化叙事、数据库叙事与网状叙事等更多元化的复杂叙事形态。这些形态是否会成为未来国产剧集的主流,我们不得而知。可以确定的是,游戏化叙事也在一定程度上唤起了受众对叙事形式的追捧、喜爱与消费诉求,提升了受众的认知与理解能力。它使影视剧在“戏剧观”“电影观”与“电视观”之外,获得了“游戏观”的艺术本体观念拓展,其理论内涵也发展成为这四者水乳交融的“四位一体”。
结语
亨利·詹金斯曾提出“叙事正在成为一种构建世界(World Building)的艺术”。可能世界叙事学为审视剧集的世界架构带来了具有启发性的视角。影视剧建构的世界不仅是“物质容器”,还是“心灵投影”:既为故事发生的“客观”环境构筑清晰自洽的物质边界,又为受众感知的虚拟时空建构完整统一的心灵图景。剧集由于拥有较长的叙事篇幅与多样化的观看方式,因而能够囊括多重可能世界,并在其中呈现出多维的人物、多变的类型、多元的价值与情感。可能世界叙事学不仅能够为时空循环剧提供分析视角,还能够为科幻、玄幻与奇幻等类型剧中的虚拟世界与幻想世界的叙事动力机制提供阐释框架。
国产时空循环剧依靠岔路情节与化身叙事形成游戏化叙事机制,通过“现实虚拟”的空间修辞策略与多元人物为故事世界拓展疆域。它同时具备了幻想气质与现实质感,充分发挥了想象力美学的优势,形成了扣人心弦与隽永动人的情感体验。
国产时空循环剧的风靡,使作为本体观念的“游戏观”逐渐融入剧集的本体观念体系。当下的媒介融合并非新媒介对旧媒介简单粗暴的形式重塑,而是新旧媒介彼此在内容、形式、结构、材质等各个层面的共享、互渗与相互借鉴。“游戏观”体现出剧集本体观念在媒介融合时代的全新发展。前一阶段热播的科幻剧集《三体》也通过嵌入的虚拟现实“三体”游戏实践了游戏化的叙事形态和“可能世界”的展开。可见,“游戏观”已渗透在剧集的内容与形式等各个层面,与“戏剧观”“电影观”和“电视观”融合成为“四位一体”的剧集本体观念。未来的剧集本体观将在新媒体技术的发展下得到进一步拓展。
未来的国产时空循环剧在循环原因与世界架构等方面应当予以强化。目前,《开端》等时空循环剧并未明确交代时空循环的根源。长此以往,便会使受众质疑时空循环的合理性与真实性,进而削弱沉浸体验。此外,国产时空循环剧应在“现实虚拟”的基础上与现实世界建立更多的关联,进而触动现实,对现实问题提出“可能”的解决方案。漫画《只有我不在的街道》与《你的名字》为此带来了借鉴。这两部作品通过故事世界的建构,分别指涉并反思了“宫崎勤事件”与“日本311大地震”等现实灾难,并通过“时空循环”与可能世界的开启对现实缺憾进行了想象性解决。
国产时空循环剧应当积极与当下的现实议题对接,实现作品的社会服务功能。虚拟世界是现实世界的“可能世界”,影视剧也为我们开启了人生的另一种可能。剧集展现的故事世界未尝不会通过“再中心化”的方式跃迁至现实,影响现实。应将国产时空循环剧视作现实世界的倒影,反思过去,展望未来。“时空循环”与“可能世界”使我们对未来抱有审慎的态度与浪漫的遐想,游戏观的拓展也让我们寄望于国产剧集未来的全新形态。借助“可能世界”的力量,与现实建立更多的通达关系,或许可以为现实的发展提供镜鉴,为影视剧的未来发展注入更多可能。
*为方便电子阅读,已略去原文注释,如需完整版本,请查阅首发纸刊。

作者:姚睿,广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