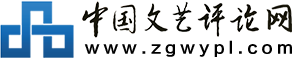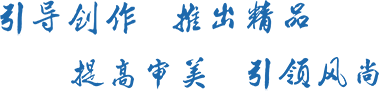身体、空间与“场”:戏剧的互联网再媒介化重塑
(第四届网络uedbet全球体育uedbet让所有玩家提款优选汇优秀长评作品,发表于《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5期,由作者参选提供)
2020年4月5日和6日晚八点,戏剧导演王翀根据爱尔兰现代主义剧作家塞缪尔·贝克特的悲喜剧改编的新版线上戏剧《等待戈多》在线上演,来自北京、武汉、大同等地的演员,挑战戏剧创作新模式,两天有近三十万用户观看。这一网络现象级戏剧演出,突破了传统线下戏剧的观演关系构成,营造了基于互联网的“线上戏剧场”,使线上戏剧正式进入中国戏剧的史册。
线上戏剧国外开展较早,但鉴于早期技术与观众接受度的局限,其在诞生之初仅作为技术加持下的艺术实验品活跃于极小圈层范围内,未被投放于广泛的群众实践当中。新时代技术的不断发展与疫情造成的线下戏剧行业式微,为线上戏剧的“出圈”提供了契机。2020年4月10日,受疫情影响,巴德学院春季大戏《MAD FOREST》转移至线上,作为特殊时期的新媒介探索,《MAD FOREST》在美国戏剧界受到广泛好评,并在同年五月受邀于外百老汇进行第二轮线上戏剧演出。除法国、美国外,英国、德国、以色列、澳大利亚、韩国、日本等多个国家也在疫情期间展开线上戏剧演出。2020年4月5日,作为国内第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线上戏剧,《等待戈多》开启了中国线上戏剧的大幕。7月19日,中国国家话剧院编剧钟海清导演的线上戏剧《白骨精三打孙悟空》于腾讯会议在线直播,引发了国内戏剧界对线上戏剧的进一步关注。全球化背景下,观众在无意识的国际戏剧比较视角中审视当代国内戏剧发展,而我国戏剧的再媒介化尝试便是对我国传统戏剧文化自觉意识与探索精神的最佳印证。
一、“线下”到“线上”观演场的再媒介化重塑必然性
媒体变革语境下,线上戏剧的“生存与毁灭”一直都是学界炙手可热的话题。“世之腔调,每三十年一变”,400年前明代戏剧理论家王骥德的这句话,似乎对全球化中今天戏剧的发展,仍有借鉴意义。所谓“腔调之变”,正是戏剧艺术应对自身“危机”而进行的自我否定。当戏剧艺术发展到自身饱和阶段时,外部“危机”刺激无法再使其产生新的能量,线下戏剧必然引发由量变产生的质变,涌生出新的形态迎接新的时代挑战。如果说戏剧上线(云戏剧)是线下戏剧在疫情危机下的被动求生,那么以再媒介化发展为目标的线上戏剧,则是戏剧艺术发展历史中的必然,是线下戏剧对互联网语境有意识地积极回应。鉴于线下戏剧艺术沉淀千年的历史根基与当下互联网技术迅猛发展的大势所趋,此类融合绝非任何一方的强势侵占,而是相互支撑、互为依存的彼此渗透。福楼拜说,“科学与艺术在山脚下分手,在山顶会合”。作为网络媒体技术与线下戏剧艺术双向融合的产物,线上戏剧的诞生符合艺术发展规律,迎合时代主流审美与生活方式,既是对传统戏剧艺术创造性地延展,亦是对未来戏剧艺术创新性地实践。同时,处于再媒介化初期阶段呈现的不稳定性,则印证着线上戏剧并不是传统戏剧艺术的终点,亦不是绝对意义上未来戏剧的起点。在戏剧艺术脉络中,线上戏剧脱胎于传统的线下戏剧,并以独立的姿态站在了未来戏剧的大门之外。线上戏剧承载的使命一方面是推动戏剧艺术以再媒介化的方式寻求向前发展之路径,另一方面必然地成为衔接传统与未来戏剧的关键枢纽。只有清楚认识了当下的线上戏剧,才能大胆地憧憬并设计未来戏剧。因此,围绕线上戏剧的针对性研究对未来戏剧的发展具有启发及推动作用。本文将就“戏剧场”在线上戏剧再媒介化过程中呈现的特点和变化进行针对性思考。
新媒体时代,线下戏剧在向线上戏剧迈进的过程中,观演关系也随之发生了颠覆性变化。观演关系构成戏剧场的核心与灵魂,所谓“观演关系”是“指演出场地(环境)的结构形式所决定的演出者与观赏者之间的特殊的审美关系。”作为戏剧艺术中的重要一环,观演关系是衔接演员、观众与表演空间的必要元素。传统的线下戏剧语境中,观演关系的形成是依靠观众与演员身体在场的直接互动,即观演双方同时身处同一封闭且固定场域内,因戏剧演出而孕育的审美关系。而在线上戏剧中,承载观演关系的“场”(观演场地)由线下转移至线上,打破了场地空间的封闭与固定性,是对传承千年之久的封闭式观演空间的破壁尝试;生发观演关系的“场”(观演在场性)由身体在场幻化为身体化在场,突破了身体观念的躯体边界,催生了欣赏式、伴随式以及多内容间离式等以个体观看为主的观看模式,促进了戏剧受众的多元化发展;而形成观演关系的审美“场”(观演审美场域),由被动互动转变为主动互动,合理化解了“线上”与“身体化”带来的观演关系脱节,通过再媒介化手段衔接并塑造了新的戏剧观演“场”。
二、意象“空间虚拟”到技术“虚拟空间”的观演场景再塑
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人们对空间的定义一直围绕宇宙物质实体展开,被禁锢于“三维”体系之内。所谓的“多重空间”或“空间折叠”多出现在科幻作品中,不受普罗大众的理解与接受,而互联网技术的出现使原有空间概念被彻底颠覆。依靠互联网技术连接产生社会互动,并在此基础上形塑而来的网络空间,是真实人群传播渠道的扩展,其生成的是一个众多的、相互影响的参与者所组成的环境空间。在释义当代空间概念的同时,信息技术也重新定义了人们如何与环境本身以及他人一起参与城市空间的多种与此相类似的,基于身体与空间的社会实践活动。线上戏剧作为戏剧艺术在互联网时代的再媒介化实践活动,与线下戏剧在物理空间层面最大的不同,就是对基于空间进行规划的戏剧观演场的再塑。
《消失的地域》一书中梅罗维茨借用劳伦斯·佩尔温的定义提出,“场景为一个特定的地方,在大多数情况下包括特定的人,特定的时间和特定的活动。”如其所言,线下戏剧的观演场景正是基于固定且封闭的剧院空间中,由演员及观众双方在指定表演时间段内,进行戏剧观演活动并于其中建构故事情景所需的场地空间。在线下戏剧中,剧院作为承载观演本体的空间容器,封闭且固定的特性决定了依靠其塑造人物及再现故事情境的舞台表演场景亦具有相似特性——固定性、唯一性、封闭性。
戏剧舞台的固定性与唯一性承接于剧院建筑位置的固定与建筑空间的封闭属性,具有绝对性意义,对戏剧舞台表演中场景划分起到决定性作用。地理位置局限背景下诞生的“地理场景”,即线下戏剧表演舞台,将所有演员与观众在同一时间汇聚一堂,传递出谁什么时候在哪里做什么,怎么做以及包括或排除谁的观演场景划分信息代码,形成由身体及身体的有效信息传递。在莎翁经典剧目《罗密欧与朱丽叶》第二场第二幕,罗密欧与朱丽叶于花园情定的段落中,在舞台布景与演员有意识地肢体表演(如罗密欧通过下蹲的肢体动作诠释躲藏的尴尬境地,朱丽叶用身体前探的肢体动作展示透过窗子眺望远处的情景等)建构中,一个舞台被巧妙且合理地呈现为“后院花园”与“卧室”两个场景。同样,在我国传统戏曲《西厢记》第一本第三折《酬韵》中,张生与莺莺隔墙互诉衷肠的戏份,经由两位演员意象化的肢体表演——如登高眺望,心急误撞墙等——使信息经转观众内心于舞台中央矗立一道无形的院墙,将同一舞台划分为花园内外两个不同空间场景。可见,无论东西方,由舞台特性所决定的表演模式及由此生成的场景划分已成为线下戏剧常态。单一空间内随观者注视而稳定的多元化场景,通过演员戏剧化表达下释放的信息符号,令观众在印象生成与空间结构获取的过程中,实现物质景观与抽象认知的有机融合,自主生成并合情判断主、次场景。
戏剧舞台的封闭性承接于线下戏剧固定化表演模式的同时亦对其产生深刻影响,两者相辅相成,具有相对性意义。于宏观层面,戏剧舞台的封闭性是相对于与观看场地的独立而言,两者各自承载不同职责,具有特定文化功能。于微观层面,其封闭性是相对于整体舞台中各个独立表演场景的塑造而言。在内置表演空间中传承千年的戏剧虚拟化表演程式,最大限度释放了被剧院封闭且禁锢的想象力,在无限延展舞台表演空间的同时合理划分表演场景,并将舞台置于坐标轴中,于不同象限建构起差异性坐标,在虚幻的舞台表演场景中投射出真实且具有封闭性的历史与现实场景,并赋予其极致真实的质感。例如,在西方古典主义戏剧中,爱情的“表达方式是飞吻和接吻,把自己的手和对方的手按在自己的心口上(因为通常认为人是用心来恋爱的)、跪在地上(而漂亮、高尚的人只是跪下一条腿,以便显得更美些,但喜剧角色要跪下两条腿,以便显得更可笑些),两个眼珠向上翻(爱情被认为是高尚的情感,在表现高尚情感时,总要向上看,就是向天上看,因为一切崇高的东西都在天上),狂热的活动(时常近乎戕害自己的肢体,因为恋爱的人不应该控制自己),咬住嘴唇,而眼发亮,鼻孔张大,屏住呼吸,热情的耳语”等。程式化表演模式极大降低了戏剧表演对资金、场地等客观因素的要求,以最简化的行为方式,突破场域空间局限,实现戏剧信息的理想化传递。同样,在“一桌二椅”中塑造宫廷禁院、军帐将台、庵观寺院、亭台楼阁、配楼山岗……,在三五演员间营造“擂鼓钟鸣,文武班齐到”效果的中国传统戏曲,亦可言深谙程式化表演之道。明代王骥德说:“戏剧之道,出之贵实,而用之贵虚。”清代王国维说:“戏曲者,谓以歌舞演故事也。”其间表达无一不揭示出我国传统戏曲程式化表演之道。在追求载歌载舞舞台美学思想的中国传统戏曲中,凭借歌舞化的意象表达手法有效调和艺术美与形式美的关系,以虚拟时空演绎、呈现真实时空原初面貌,还原普罗大众于潜移默化间约定俗成的得其形而知其神的审美参与。可见,中西方戏剧虽形式有别,但本质上却同根同源。宏观与微观层面的相互扶持使得传统线下戏剧观演空间,显现出外在形态空间与内置表演空间的一体两面,凭借意象的创设、意境的营造,为观众提供身临其境的“真实感”,形成依靠意境生成的“空间虚拟”。
梅罗维茨认为场景的边界性质决定了场景的分离程度。与线下戏剧观演场景边界的相对封闭性而言,线上戏剧的观演场景边界则具有绝对的开放性。作为传统线下戏剧艺术的技术外延,互联网语境下的再媒介化戏剧产物——线上戏剧,凭借摄像机或计算机摄像头捕捉表演画面,利用互联网进行信息传递的模式,彻底颠覆线下戏剧由身体及身体的传播途径,改变并再塑线下戏剧在同一“地理场景”中依靠意象分割舞台再造多元场景的“意象—空间”模式,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依靠逻辑链条串联的,线上戏剧特有的“技术—空间”模式,即由分割性戏剧空间向组合性戏剧空间的转变。1977年,在现场视频直播及卫星技术的双重支持下,由Kit Galloway和Sherrie Rabinowitz编导的“卫星艺术项目(Satellite Arts Project)”(图一)被视为最早的线上演出尝试,该表演首度打破表演艺术中的物理空间边界限制,使身处不同地理场景的几位艺术家在同一时间段内实现了“同台表演”的默契配合,通过对表演场景的组合,创设了一个“没有物理界限的表演空间”。以任意地理场景为表演舞台,以任意显示终端为呈现舞台,线上戏剧将戏剧表演与舞台呈现划分为各自拥有独立空间但必须共生共存的两部分,在互联网技术的连接下,生成于两个或多个表演舞台中的戏剧场景被连结为同一场域中的“虚拟空间”,并通过逻辑链条的串联最终展现于呈现舞台,无限扩大了演与演、观与观、演与观之间的物理距离。同时,技术涉足下的传统艺术在媒介场景感的营造中亦增强城市日常互动,使公民自觉形成依靠数字技术重嵌城市环境的理念,推动跨越身体空间的观演关系逐渐趋于日常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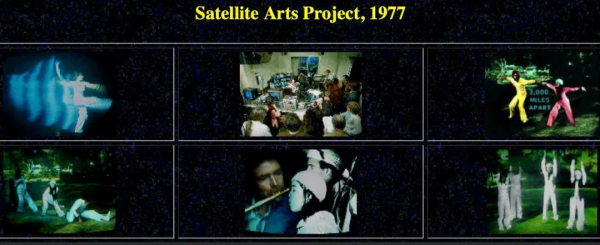
(图一)《卫星艺术项目》(Satellite Arts Project)
三、“身体在场”到“身体化在场”的观演在场性再塑
历史层叠改变了我们对于位置的身份观念,有关身体在场的认知被不断刷新。亚里士多德时代,在场源自于对事物模仿性的再现,即演员触发于心而形之于外的整体性模仿,与观众触发于外而行之于心且产生共鸣的内模拟。罗格科普兰看重“在场”的空间意义和交流功能,在《媒介的在场》中其将“在场”界定为“推进演员和观众之间交互作用的舞台演出的建筑和技术空间层面”。从携带自己的肉身到离开自己的肉身再到进入其他的身体,线下戏剧在向线上戏剧发展的再媒介化过程中,其观演在场性也历经着凭借肉身达成意义传递的身体在场转向依靠机(机器)身(身体)耦合实现意识空间交流的身体化在场,即虚拟在场。
线下戏剧强调身体的在场,无论观者还是演者。罗兰·巴特认为戏剧艺术的独特魅力来源于表演过程中身体的在场,因为“在所有的形象性艺术中(电影,绘画),惟有戏剧提供躯体,而不是它们的表象。”与雕塑中无生命的身体在场,绘画中凝固的身体在场,电影中平面的身体在场,以及舞蹈中脱离生活常态的身体在场相比,戏剧中的身体在场涵盖了视觉、听觉、嗅觉、触觉等多方面感官体验,更具生命的气息、动态的韵律、立体的形象,以及生活的平实。虽然,当下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冲击了戏剧观演中身体在场的绝对性,但在彼时确也称得上戏剧领域的金科玉律。而作为承载“观”“演”的本体,线下戏剧中的身体感知亦具有双向互动的属性。观演的身体在场有意识地将“戏剧核心三要素”(演员、剧本与观众)汇集在同一地理场景——演员与观众共处同一剧场空间内,或演绎或观看戏剧——并在观演中达成某种身体间的感知交流,凭借身体输出与接受实现戏剧艺术的传播与内化,于无意识中确立身体在场的戏剧观演仪式与秩序,创设戏剧艺术特有的基于身体在场的观演关系。
雅克·德里达认为“戏剧是力量的角力之下差异的原创性重复”,即戏剧艺术的魅力来自于舞台表演的不可复制性与不确定性。线下戏剧依靠观演两者同时身体在场所创设的实时互动,使得融合不可复制性与不确定性的戏剧舞台魅力得到极致彰显。在生物学中,DNA具有的差异性与不可重复的序列组合方式,使得经由不同个体身体形塑而来的同一戏剧角色存在天然的不可复性差异。《占花魁》出自明末冯梦龙白话小说《醒世恒言》,后经明末清初戏曲作家李玉改编为剧本演出,但凭借不同人物体态以及对戏剧角色的差异性理解,不同戏剧表演艺术家对于同一角色的塑造亦可呈现多元样态。以王芳与沈丰英为例,同为昆曲表演艺术家,王芳扮演的花魁辛瑶琴和谐恬静、温柔多情,而沈丰英演绎的花魁则放荡不羁、浮荡顽劣。其中虽有剧本设定因素,但演员对于角色的二次创造亦不可忽视。同时,地理环境、观演氛围、个体情绪等诸多不确定变量因素也在无时无刻不影响着演员及观众对自身角色的塑造,使得经由同一演员扮演的不同角色亦具有极大差异。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国家一级话剧演员宋丹丹,在从事话剧演出的40年中,出演话剧20余部,塑造了多个令人印象深刻的经典角色。《白鹿原》中敢爱敢恨的田小娥,《回归》中风韵典雅的罗扎,《万家灯火》中艰辛亦坚强的何老太太……在宋丹丹地鲜活演绎下,不同角色拥有了不同的生命与命运。身体在场的不确定性成就了戏剧舞台表演的历久弥新,依靠身体在场的线下戏剧观演活动,在不可复制性与不确定性间,应和“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树叶”的哲学名言,最大限度提高了戏剧艺术独一无二的魅力。
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冲击了传统时空布局,有关身体的再媒介化认知被再度刷新,海勒说人类有两个身体,“表现的身体以血肉之躯出现在电脑屏幕的一侧,再现的身体则通过语言和符号学的标记在电子环境中产生。”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推动了媒介与社会的共生关系,使媒介从狭隘的信息中转载体中突围而出,成为塑造与承载信息本身的形式与结构。在《理解媒介》中麦克卢汉提出“任何媒介的‘内容’都是另一种媒介”,媒介与内容的身份叠加使得媒介寄居成为常态,正如身体是戏剧的内容,戏剧又是线上戏剧的内容。线上戏剧特有的观演模式使得观演者在与同质媒介(线下戏剧)平行的同时,又在“再媒介化”(线上戏剧)的过程中不断编织新的影像文本,彻底打破身体在场的观演场域关系,形成身体化在场的新型观演关系。2020年9月4日,由青年导演贺天丁发起的“第一届维·国际现场虚拟演出展”展开了为期一个月的线上演出活动,共展演包括线上戏剧在内的25部线上演出作品。其中《味》《此时此刻》《Flight》等国内外线上戏剧广受好评,而其大多作品的主创团队、演员团队、制作团队在排演过程中都是横跨多省、市,甚至国内外联合作业,在运用互联网线上技术实现实时舞台调度的同时,令创作者、演员、观众打破空间局限、跨越身体桎梏,依靠导、演、观的身体化在场促成线上戏剧观演的完整性。从地理场景到虚拟场景,从身体在场到身体化在场,线下戏剧的再媒介化让身体以另一种形态回归在场。凭借互联网传播技术,线上戏剧打破了身体固有边界,突破了“身体实现知觉粘连的无处不在”,使身体全局性地投身到知觉活动中,并向无数视角开放。依靠摄像机或电脑终端摄录设备记录真实身体运动影像,通过互联网线上传输信息并远距离成像于多个移动终端设备显示屏,使虚拟身体与场景化世界生成融合,凭借身体在场窥视身体化在场中虚拟身体与另一时空环境实时生发的关系反映,令身体化在场替代传统意义上的身体在场,成为朝向未来戏剧实存以及立足未来戏剧之中的重要因素。
从线下戏剧到线上戏剧,身体的再媒介化促成了由基于DNA序列组合的原生态不确定性过渡到依靠技术的舞台展演不确定性,始终捍卫着戏剧艺术最独特的魅力。但以互联网为传播媒介并借助移动终端设备在线直播的线上戏剧形式,却也受到诸多质疑,其中最为突出的便是其与舞台艺术、影视艺术等艺术形式的边界划分。作为专为线上呈现的戏剧艺术,身体化在场除解构原有戏剧舞台概念外,其与线下戏剧艺术最大的不同便是对影像“剪辑”的处理。线下戏剧艺术的实现基于观演双方的身体在场,通过演员的身体表演直接成像于观众的视网膜之上,因而无法实现对剧情内容的瞬间剪辑,仅可通过闭幕、启幕的方式实现场景转变与场次转换。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实现了舞台上的创新,在表现李侠与兰芬由同志变为伴侣的过程时,采用了三对同样妆扮的双人舞演员在舞台同一空间起舞,呈现出李侠与兰芬从初见到相知,由同志到爱人的不同时间的故事,实现了“舞台拟态蒙太奇”,但是这种实现要借助现场观众的大脑进行“剪辑”形成完整故事线,这是舞台表现的创新,是舞台表演借助影像思维的有益探索。而线上戏剧借助成像窗口(直播软件)的自由切换就可轻易实现类似于影视的画面构图与转场剪辑效果。例如,在“北京国际青年戏剧节”的德语线上戏剧《九死一生》中,演员通过将叉子横在自己与镜头之间模拟门缝的方法实现场景转换;在维·国际现场虚拟演出展的展出作品线上戏剧《味》中,两位演员通过在两个对话框中同时用纸巾擦拭镜头的方式完成场景的转出与转入,达成线上戏剧中对场景的剪辑。虽然拘泥于线上的表达限制,在影像呈现中线上戏剧常常以隐喻性手法借鉴或模拟影视艺术表达方式,但这并不意味着线上戏剧在与线下戏剧划清界限的同时又倾向了影视艺术。作为一种加持手段,“剪辑”手法在扩大线上戏剧身体边界的同时,也引发了由身体本体在场的戏剧作品与身体表象在场的影视作品在影像呈现上的部分重叠,虽然表面看来线上戏剧与影视作品的界限发生模糊,但载体共性早已决定了艺术的通性,显然,这种辅助性技术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戏剧艺术的本质内涵。其中,线上戏剧区别于影视的本质不同便是线上戏剧保留了线下戏剧的实时性传播,并从根本上弥合了影视时间的碎片化与随意化。在线上戏剧《MAD FOREST》的排演过程中,导演Caryl Churchill通过聘请专业技术团队重新编程“ZOOM”(云视频会议软件)的方式,实现了对线上戏剧的实时调度与转场,通过摄播同步的身体化在场营造出替代“在场性”的“在场感”。可见,线上戏剧与影视等艺术形式存在部分重叠,但这种基于互联网技术产生的必然交集,却也正是成就并捍卫线上戏剧独立性的重要属性。
四、被动互动到主动互动的审美场域再塑
在《被解放的观众》中,朗西埃提出表演剧场中权力结构不平等现象来自于观看者本身的被动性。自戏剧诞生以来,很长一段内演员作为戏剧绝对且唯一主体拥有不可撼动的地位,而作为演员对立面的观众则长期处于失语状态。1876年,法国戏剧理论家F·萨塞在有关戏剧本体的讨论中提出“观众说”,观众首度作为戏剧本体被戏剧历史所直视。针对观众在戏剧艺术中的本体地位,我国戏剧艺术教育家何之安提出“观众不仅是演出的对象,也是演出的参与创造者。”肯定了观众在戏剧演出中的意义与创造性作用。而作为戏剧本体中的重要角色,有关观众的讨论自此也再难逃离与时代语境更迭的结合。从线下戏剧的被动参与到线上戏剧的主观互动,戏剧艺术以互联网技术为天然“屏障”,摆脱了线下戏剧观演场域中依靠封闭性地理场景渲染及强化的审美观念强加与移植,通过权利的平移与让渡,重塑线上戏剧观演场域,实现线下戏剧观演审美场域的再媒介化。
列菲伏尔认为权利遍布于空间。在线下剧场中,观众席是专属观众的权利空间,在观看戏剧的过程中观众可通过鼓掌叫好或嘘声喝倒好等肢体行为表达出自己对演员及戏剧的认可与否定,亦可通过亢奋、悲悯或冷漠、无视等细微情感变化传递出自己与戏剧的情感共鸣或交流障碍,并凭借以上身体行为来执行自己的审美权利。因而,无论是哪一种权利的执行都离不开身体这一媒介,在通过身体释放情感的过程中,观众也实现了对戏剧创作的创造性生产,在吸纳与释放间建构了专属自我的审美场域。但作为戏剧审美场域的空间载体,剧院承载观演审美活动的同时也限制了观众对于戏剧审美的自由抒发,而这种限制则来自自我身体对他人行为的反应,即于无意间完成的“模仿反射”。模仿反射是指人们在面对他人的行为动作时,相应兴奋的镜像神经元会通过模仿他人动作的行为来洞悉他人的情绪及社会意图。剧院封闭、幽暗的先天条件为观众间的模仿反射创设了天然温床。当一个或几个观众被触及自己情感的戏剧故事或表演影响时,其通过释放身体执行的审美批评权利显然会在无形中引起更多人的模仿反射,形成或掌声雷动或唏嘘一片的效果。此种效果的生成对于当事人而言是权利的有效执行,但对于通过心理暗示保持与周围环境高度一致的胁从者而言,却是权利的干预,一种于无意识间完成的审美入侵。但在线下戏剧观演场所云屯蚁聚的观演模式下,基于模仿反射形成的观众被动互动却也在所难免。因而,虽然观众在观看戏剧表演时会依靠自我审美判断行成专属审美场域,但在不断的摩擦碰撞中,其终会建构起趋向于团体性的审美场域,于无意识中接纳由被动互动带来的权利让渡。
相较于线下戏剧相对稳定的受众群而言,线上戏剧特有的互联网属性决定其会拥有更多且更为复杂的受众群体。这种复杂性不仅表现为年龄、职业等外在形态,还体现于催生其观看戏剧的不同欲求,以及承接于欲求的观看模式。因此,在戏剧的再媒介化研究中,对受众观看欲求及模式的探讨必然成为题中应有之意。日本学者河竹登志夫曾在线下舞台戏剧演出的研究中,就关注了观众的创造性作用,他认为如果仅将观众作为具有强大力量的物理性参与者来认定观众的创造性参与是片面的,在观演关系的构建过程中,其应然表现为在舞台与观众中以炽热的气氛来消除冷默的状态。所谓物理性参与即观众直接参与戏剧表演,例如线下戏剧善于运用群众性的氛围渲染,使更多观众通过情感反馈的方式被动参与其中。所谓创造性参与,即通过演员与观众的有机互动,使观众主动参与戏剧表演。而在线下戏剧的再媒介化过程中,不仅观众的主动参与权得到保证,捍卫参与权的观看模式也进一步迈向多元化发展。2020年4月5日,被称为中国首部线上戏剧的《等待戈多》被搬上腾讯视频艺术频道,“形式革新+内容创新+现场直播”的方式使得18万人同时驻足“观演现场”,在创下中国话剧最多单场观演人数记录的同时,也拉开了我国线上戏剧观演模式的大幕。而伴随这场戏剧盛宴同时拉开帷幕的还有专属于线上戏剧的多元化受众观看模式。欣赏式观看、伴随式观看、多内容间离性观看等众多观看模式的出现不断丰富并发展着技术加持下的当代受众观剧模式,迎合了不同需求下的受众欲求。所谓欣赏式观看即用享受的心态,悠闲的姿态感受、领悟戏剧表演中的情趣。在这种观看模式的引导下,戏剧作品被定义为一件精美的艺术作品,观者赋予作品以肯定意义,其观看的本质目的是满足自身的观看欲求,而这种欲求的理想化状态便是不受外界环境影响,可自主感受、领悟,并主观参与其中。这种缺席于线下戏剧,无限接近于纯粹观演且看似无法实现的观剧理想化状态在线上戏剧中得以实现。在线上戏剧中,演员各自的表演舞台区域与观众各自观看表演的“观众席”空间被互联网通讯技术独立分隔开来,并进一步促成身体空间的独立。而观众身体空间的独立则保证了其审美自主权的独立。18万人观看的直播室即18万个相对独立的观演空间及审美场域。线上戏剧中一闪而过的文字讨论则可使观众不被鼓掌、叫好等有声氛围影响,形成更加客观化的观演欣赏式评价。同时,线上戏剧自主选择开启或关闭弹幕的形式也最大限度保障了观众自我审美场域与自我审美认同的双向建构。通过再媒介化搭建文本内部空间与人类真实空间的桥梁,摆脱线下戏剧中因身体“模仿反射”导致的权利弱化,使个人独立环境下的个体性被最大限度予以保存。与欣赏式观看所追求的个体独立性相反,伴随式观看更加侧重观看效果中的群体性意义。要了解伴随式观看首先要明晰伴随式概念所涉及的两个维度:时间维度、空间维度。时间维度上的伴随是一种自戏剧表演开始至结束过程中带有时间跨度的陪伴,在这种观看模式的暗示下,观众在观看表演前不对戏剧作任何主观情感移植,全程以一种批判的视角观察戏剧表演,肯定与否定并存,接纳与摒弃共存,其观看本质是在戏剧表演中完成探寻与发现,满足自身的表达欲。正如,线下观演中依靠身体的戏剧反馈被弹幕、留言、点赞等方式替代,观众的实时反馈不再局限于无声的身体动作或简单的语气字词,弹幕等方式的实时反馈在遵守观演秩序的同时,更加直观化的表达了观众对于戏剧的看法及评价。空间维度上的伴随即观剧过程中的群体性陪伴观演,与线下戏剧通过身体在场所营造的群体式空间陪伴有异曲同工之处,其所追求的是在时间维度伴随基础上形成的戏剧批评的被认同,即一种源自强烈社会认同感的亲近欲。此外,时间维度与空间维度上的伴随并无先后、主次之分,戏剧审美与审美社会认同的渴望使得传承于线下戏剧的群体性场域在线上戏剧中展现出全新的面貌。得益于电子信息技术支持下弹幕、留言、点赞等形式的在线沟通方式,这种实时交流以观众“在场”的形式达成了观众对于虚拟舞台空间幻想的建构,使无数独立审美场域在保持自我的前提下汇集为一个整体性的审美场域,实现了戏剧观演间的整一性建构。多内容间离性观看与伴随式观看在概念维度分类上相同,亦分为时间与空间两个维度。时间维度上的多内容间离性观看是指观众在戏剧表演过程中,因线上戏剧独特的多屏模式所产生的主观间离,即在多屏共存的表演界面中观众可以自主选择观看对象,主导自我情感移植与抽离并重新投入下一对象的时间节点,最大限度激发了观众的求知欲。空间维度上的多内容间离性观看是指观众在观看戏剧表演的同时可以自由搭配其他事情。线上戏剧对线下戏剧封闭观演空间的破壁,瓦解了传统观演秩序对观众的实在制约,赋予观众更大的空间活动权,这种观演类似于泡沫剧的陪伴式互动,不仅拓展了线上戏剧的受众群,更令戏剧作品的社会意义被不断延展。作为一种潜藏的“说服”方式,戏剧对于观众的“暗示影响”同泡沫剧的强“培养性”一样,是不可忽视的。研究者认为,泡沫剧的强培养性不但会促使他们认知的改变,还会改变他们在现实生活中的行动,而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正是线上戏剧中多内容间离性观看模式期待给予受众的。线上戏剧基于互联网技术所生发的观演场域迎合了时下受众的多元化观看欲求,从观看及互动多角度实现了由被动到主动的审美场域再媒介化建构。
五、结语
互联网语境下媒介介质的交相融合,与符号文本的再编码传播使得传统艺术的“再媒介化”成为当代艺术形象存在的主流方式之一。线上戏剧通过“再媒介化”手段整合观演空间,突破线下戏剧因地理场景与个体身体唯一性所禁锢的观演空间,使由身体化在场主导的戏剧观演替代传统身体在场的戏剧观演,最大限度放权于观众,实现了自我审美场域与审美认同的双向建构,生成新型话语场。以解构和重塑戏剧观演关系为目标的线下戏剧再媒介化,正不断改变戏剧艺术的外延与内涵,丰富戏剧生态系统,使之呈现新的活力。因而,从线下戏剧到线上戏剧的戏剧发展生态角度窥伺可发现,传统的线下戏剧坚守的戏剧理念是让观众走进剧院,即让观众走向戏剧。但在互联网语境的大势所趋下,当代线上戏剧秉持的让戏剧走向观众的戏剧传播逻辑,更加符合高速流转的时代语境下人们对艺术的欲求及要求,是对“uedbet全球体育为人民服务”的有力践行。
*为方便电子阅读,已略去原文注释,如需完整版本,请查阅首发纸刊。

作者:史册,东北师范大学传媒科学学院(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邵仁焱,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