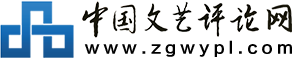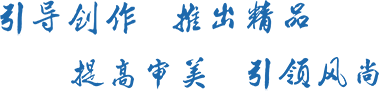小品、游戏与“白日梦” ——论竖屏微短剧的戏剧特征及其文化逻辑
(第四届网络uedbet全球体育uedbet让所有玩家提款优选汇优秀长评作品,发表于《中国电视》第2022年第9期,由作者参选提供)
对于中国人而言,“竖”着看并不能算是太陌生的经验。这一经验,从竹简木牍时代的汉字书写与文章阅读就已定型,记载并陪伴着中华文明的荣光与不屈。只不过近代以降,中西文明的交流碰撞才逐步让“横”着看成为人们交互信息的主要姿态。有趣的是,今天智能手机时代带来的竖屏观看并不是“似曾相识燕归来”的历史经验回归,而是“科技改变生活”的审美习惯建构。看起来,“竖”的视野大约总没有“横”的世界来得开阔——因为人的视线更适合于平行线上的移转延伸。但无奈的现实是,除了在游戏或观影等沉浸式情境中手机有机会“躺平”之外,社交、电话、刷屏,大多数的手机使用情境显然是“青松挺且直”。
因此,“竖”的视野对于人们而言是习惯成自然,对于技术开发者而言是时不我待的新时空,而对于心中有梦的商家而言则是一片浩瀚的蓝海。在这样众人拾柴火焰高的背景中,竖屏微短剧的悄然出现乃至蔚为大观当然就显得合情合理。从几年前爱奇艺《生活对我下手了》的初步尝试,到今天抖音、快手等超级短视频平台的大力推送,无论从生产规模、戏剧特征、制作手段还是传播效果来看,竖屏微短剧都已然成为一种全新的网络剧形式。关于它的讨论,不应该再纠结于它是不是“剧”,而是应该探讨它是一种怎样的“剧”以及它未来会有什么样的想象空间?

《生活对我下手了》海报
一、文本样态:竖屏舞台的连续性“小品”
当下流行的大多数竖屏微短剧葆有了竖屏短视频浓郁的自媒体草根基因。观众们并不会特别在意某部剧的导演、编剧或者演员是不是有着赫赫声名,而是更多地被抖音博主、快手达人、B站up主等影像生产者的“个人”魅力所吸引。在浩若烟海的短视频生产中,自媒体人成为网红脱颖而出是一件极为困难的事。因此,无论乡村、萌宠、旅游、美食、美妆、知识等何种垂直分类题材短视频,要想集聚受众的注意力,大抵必须具备两个要素,即故事性与表演性——有创意的故事抓人的心,有意思的表演抓人的眼。在竖屏微短剧的舞台上,这两个元素显然被承继发扬,但是,既然成为“剧”,故事的创意不能只是灵光乍现,演员的表演也不宜即兴随机,它们大体上必须被纳入规定的戏剧情境中,成为连续性、系统性的戏剧构成要素。
较之于横屏剧,竖屏剧的表现时空受到极大的框限。首先,摄影机的腾挪运动无法自如地展开,既很难在平行视线中呈现广阔的背景,也很难在纵深视线中呈现层次的区隔;其次,之于演员的表演,舞台常常被限制在镜框之中,你很难指望有群戏的出现,群戏在视觉上会极为逼仄;再次,镜头与演员的调度走位配合也会变得颇为不易,因为穿插的走位很容易跑到镜头之外。但硬币的另一面恰恰在于,当沿袭已久的创作习惯不再适应“竖”的形式框架时,一套新的影像文本创作语法便会渐趋成熟。本文选取了抖音、快手等主要短视频平台播放量过亿的20部典型竖屏微短剧进行观察,其文本特征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绝对的主人公聚焦。竖屏舞台的呈现通常只容纳一到两个主人公,配角的功能主要是穿针引线、插科打诨。一个主人公是独角戏,比如《小心!有点不对劲》中天赋异禀的小女孩步美,总是能敏锐地觉察到外部世界的危险,步步惊心但却一定会绝处逢生,进而机智地帮助身边人摆脱险境;《莫邪逆袭记》中的职场女强人莫邪,在每一集中,都会遇到不同的对手或要帮助的对象,配戏的演员走马灯似的不停变换,只留下莫邪一个人神机妙算、胸有成竹的洒脱身影。两个主人公是对台戏,比如《我的房东奶奶》中,因为年龄、性格、文化的差异,刚刚毕业走入社会的田小野与古怪固执的房东奶奶在日常生活的冲突此起彼伏,构成了几乎全部剧情;《超级保安》中化身潜入豪门的小保安,与外表强硬内心脆弱的女总裁,两个人的爱情攻防战与商场守卫战贯穿全剧始终。这些剧集中主人公的强势地位显然一定程度上为竖屏剧镜头的聚焦优势所决定。主人公的仪表、姿态、表情、言语成为竖屏剧最刻意放大的表现内容,在近距离的手机观看中,主人公也极易与受众形成“面对面”的交互体验。换言之,在持续的刷屏过程中,或许剧情的张力会被“脸”的魅力所替代,人们不像观看电视剧时容易沉浸在令人难以自拔的故事世界中,而是会跟随“可触可感”的主人公一起若即若离地穿行于现实与想象时空。
第二,“快讲”与“快切”相契合的剧情逻辑。较之于横屏微短剧渐渐被纳入精品化生产、单集时长向中视频靠拢的趋势,典型的竖屏微短剧单集时长一般控制在1到3分钟,节奏通常也就更为明快跳跃。体现在故事层面是“快讲”,作品通过大幅度的压缩与剪裁将情节在方寸屏幕上展开。比如非连续剧情的《生活对我下手了》中,辣目洋子化身为各种家庭角色与社会角色,每集讲述一个辛辣活泼的小故事,吐糟在生活中遇到的不易与陷阱;连续剧情的《通灵妃》将顶替进王府的千云兮小姐与夜幽冥王爷的爱情切成快速翻转的短故事段落,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喜剧桥段接力推出。体现在技术层面则是“快切”,在竖屏微短剧的影像制作中,后期剪辑很明显地替代前期拍摄成为了核心技术元素。运用对比、平行、交叉等蒙太奇方式,摄像机的相对静态画面通常会在二次剪辑中被切条组接成匆匆流动的快速动态画面。非常典型的例子是,在横屏影像中非常经典的表现人物关系的正反打镜头,在竖屏微短剧中因为镜框限制大多变形为“正反切”镜头,即A、B角的越肩镜头及侧方位的小全景镜头并不多见,而大体上被A、B角交替表演的正面向镜头所替代。有时为强调对立,上下分栏的A、B角同框镜头也间或被呈现。如此,演员似乎是在故事情境中相互交流或冲突,又似乎像直接站在舞台上向观众表演。这种表演某种意义上突破了手机屏幕或者舞台“第四堵墙”的阻碍,给观众带来了提示性的“间离”感受。
第三,环境虚化与语言中心。作为戏剧的重要构成要素,环境的表现在竖屏微短剧中很难出彩。一方面是因为制作成本的限制,另一方面是镜头表现力及剧集时间的束缚,环境在大多数作品中是符号性的存在,如果背景是城市,那么镜头通常框定十字路口或者街巷角落;如果背景是农村,那么镜头大概会守在农家院落或者乡间阡陌;院落如果背景是公司,那么镜头习惯性地会指向办公隔间或者会议场所;即使镜头登堂入室、进入家庭,观众其实也很难看到居所陈设的全貌。事实上,当面对观众侃侃而谈的主人公占据了竖屏面积绝大部分比例时,观众们便不会太在意环境是自然风光还是人文风景。这时,类似于舞台戏剧的布景,竖屏剧的环境呈现作用主要在于提供给演员一个设定的表演空间——这一空间的局促也决定了演员必须主要靠语言以及修饰语言的表情来吸引观众们的大多数注意力。竖屏剧的人物语言特征一是快人快语,迅即且密集的台词可以极有效率地交代情节;二是唇枪舌剑,对手戏里极刻意的言语交锋可以帮助剧情的推进或回溯,比如《律政奶爸》中律师和幼儿园老师的情感故事几乎全部靠三两个人的对话牵连组织;三是夸张渲染,流行语的大量嵌入、语气助词的随机堆砌、对白腔调的抑扬顿挫,让人物语言充溢日常气息与民间氛围,大多数竖屏剧也因此呈现出活泼的喜剧风格。
总体而言,作为网络微短剧中的一类崭新样态,竖屏微短剧开始逐步发展出一些辨识度较高的文本特征。无论主人公的强势地位,快速的叙事与剪辑节奏,还是虚化环境中的语言之流,都极适于帮助凸显演员在竖屏舞台上的卖力表演。如果要类比的话,竖屏微短剧的表演非常像剧场或晚会舞台上的小品表演。只不过,竖屏微短剧的剧集容量远超小品,剧情紧密关联的作品剧集通常在20集到40集之间,剧情不关联的作品理论上剧集没有任何限制,可以一直更新到生产者或受众某一方放弃。如此看来,当下的竖屏微短剧可以看作是一种连续性的影像小品。小品虽“小”,但已然是一种雅俗共赏的戏剧形式;当然,小品之所以“小”,也正因为它与经典意义上的舞台剧、广播剧、电视剧等戏剧形式还有着创作力度与深度的距离。
二、叙事成规:类型杂糅的戏剧“游戏”
热奈特指出,“叙事”(narrative)包含三个层次的概念:话语(discourse)、故事(story)和叙述行为(narrating),他认为三者之间是素材、呈现结果和怎样呈现的关系。尽管人类社会的叙事文本形态千变万化,但叙事组织与叙事策略的规则却大抵有章可循。就文本个案而言,微观的叙事组织常有“套路”,宏观的叙事策略常有“模式”;就文本比较而言,横向度的合并同类项可以归纳出“类型”,纵向度的追溯历史可以考证出“原型”。这些叙事成规往往既或隐或显地体现在作品之中,又潜移默化地根植在受众内心。在这个意义上,当竖屏微短剧直面手机屏幕前千千万万的网民时,它面对的其实也是被电视剧、网络剧培养起来的受众审美习惯与心理定势。对追求速度、效率与效益的竖屏剧创作者而言,叙事的突破与创新多少显得奢侈,而模仿与搬用成为他们普遍采纳的叙事选择。
一方面,竖屏微短剧呈现出非常典型的类型剧特质,或者说,它们干脆就是竖屏缩微版的类型剧——剧情缩微的同时类型元素反而会被进一步集中放大。比如《通灵妃》《凤求凰》等俊男美女的传奇演绎,对应的是古风偶像剧,但古风的服化道装扮的架空布景更为彻底,曲曲折折的爱情才是全部真相;《莫邪逆袭记》《月野你马甲掉了》等商业领域的夸张故事,对应的是都市职场剧,但职业人生的成长与感悟大多被剥离,作品要的就是刀光剑影的冲突与反转;《金牌婆婆》《女人的觉醒》等呈现出的普通百姓的市井人生,对应的是家庭伦理剧,但家庭关系背后的社会时空背景却不再明显,婆媳、夫妻、父子之间的矛盾往往会成为单集故事的“爆点”;《再不恋爱就要过期了》《我怎么这么好看》等青年男女的恋爱故事,对应的是都市爱情剧,只不过爱情不再附丽于生活,“为爱而爱”的桥段成为创作者的不二选择;《我和我爹和我爷》《俺娘》等农村生活的情境再现,对应的是乡村情景喜剧 ,但“土味”的语言和表演却几乎承包了所有的笑点;《小心!有点不对劲》《小五探案录》等充满悬念的惊奇故事,对应的是悬疑推理剧,但剧情的瞬时转换不会留给观众更多“烧脑”的时间,而会不断带给观众谜底马上揭晓的愉悦快感。
另一方面,大多数竖屏微短剧并不会拘泥于某一特定类型的标签限制,而是抱着一种实用主义的创作态度,熟悉的桥段随手嫁接,吸睛的元素任意点染,搞笑的包袱信手拈来,让剧集呈现出类型元素杂糅混搭的表现风格。以总剧集数超过500并还在不断更新的抖音爆款竖屏剧《超级保安》为例,其第一季的主要类型元素还是爱情偶像加职场商战,作品融霸道总裁“爽感”与玛丽苏爱情于一炉,单集故事随机生成,移植、戏仿、改编各种喜剧桥段,吸引并积累了大量粉丝,并逐步形成了自己的lP标识。在此基础上,《超级保安》一气从第一集推进到第五季,原有故事架构不够用就另起炉灶,让小保安杨有三彻底地玩一次穿越,于是现代元素与古风背景任意穿插,拯救、对抗、圈套、考验等叙事技巧不断叠加,美食火锅、服装拍卖、拳击比赛、广场舞等也登上宫廷殿堂。这样的竖屏无厘头神剧实际是当下影视剧中各种类型元素的集萃,虽然浅薄甚至让观者略感尴尬,但你若将之当作一两分钟的作为生活调味品的影像游戏,能够开心一笑,便不会太在意它是否合情合理,是否深入人心?
由此看来,游戏性是竖屏微短剧的显著表征。其一表现为创作者的自由,并不需要太高的成本。尤其是对于自媒体创作者来说,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并不需要周密的前期策划、完整的反复修改的剧本。创作者经常处于一种现在进行时而非现在完成时的工作状态,因为先期作品投放播出渠道后,创作者可以根据市场情况和受众反馈,随时在更新的过程中对后续作品进行修改调整,船小好调头,试错成本较低。比如《再不恋爱就过期了》在男主演退出拍摄后,直接更换演员也无碍剧集的延续。此外,鉴于社会“趣味一直处于流动之中”的现实, “新的趣味共同体不断生成,旧的趣味共同体不断瓦解。”且播出且生产的工作状态也让创作者可以随时在剧集中补充社会生活与流行文化的新内容,从而保持影像文本的“趣味”与新鲜度。其二表现为传播者的自由,大多数竖屏剧作品既有原创方的点对面传播,也有大量自媒体和网民转发的网状传播;既有平台独家扶持激励的圈内传播,也有跨平台散发的跨圈传播;既有完整剧集的打包整体传播,也有化整为零的切条视频传播。人们很少听说有关于竖屏微短剧的播出版权纠纷——其基于短视频平台的蓬勃发展天然地带有了众众传播的基因,商业逻辑也与传统电视剧、网络剧大相径庭。其三表现为观看者的自由,在源源不断的产品供给中,受众们有选择作品的自由,也有选择剧集的自由。他们的观看时间是随机任性的,往往是在生活的片段中与影像的片段相触碰,因此,他们不会太在意特定的演员、导演或者编剧,对于他们而言,竖屏微短剧更像是召之即来的影像游戏。更有意味的是,他们可以将观看者的身份随时置换成传播者,甚至晋级成为创作者。这种自由流动的生产传播图景中不断交互着人们的戏剧经验——而戏剧经验本质上就是浓缩的生活经验。
三、文化逻辑:加速时代的造“梦”流水线
作为一类崭露头角的影像文化产品,竖屏微短剧的广受欢迎背后有着鲜明的时代印记。 哈特穆特·罗萨曾经就现代社会的速度表征做过精辟的分析,他认为“科技加速、社会变迁加速,以及生活步调的加速,已经形成一种环环相扣、不断自我驱动的反馈系统。”在一个匆匆忙忙奔流不息的加速时代里,人们不像“从前慢”的时代里有充裕的整块时间——时间往往被各种事务秩序切碎。然而人们对于影像产品的需求并不因此而减少,影像是时代之镜,也是人们的生活之镜。“正是现代社会中影像生产能力的逐步增强、影像密度的加大,它所涉及到的无所不在的广泛领域,把我们推向了一个全新的社会。”只不过,影像产品的外在形态及接受方式也必须逐渐演变以适应人们的时间安排。比如之于电视剧的倍速观剧成为青年人的习惯方式,短片组合的集锦式电影让人们在影院里一次性看到更多故事,而“三分钟看电影”之类的影视快剪尽管引发版权争议还是广为传播。竖屏微短剧的“短”无疑也正体现了文化生产的速度逻辑,能够迎合人们在通勤、等候、小憩等碎片化时间中的手机观剧需求。
速度逻辑背后的推手是无所不在的商业逻辑。有论者在分析短视频文化现象时说,“资本涌入与技术跃进的结合,推动短视频成为当下社会最风行的影像形式。人们生产的各种短视频景观,不管是否有着明显的功利目的,都在无形之中被标注了以观看量和点赞量等为“货币”计量方式的价格。”第一层面,让短视频成为当下社会风口产业的显然是商业资本与超级平台结成的同盟;第二层面,当短视频场域本身充满白热化竞争的时候,网络微短剧作为细分产品成为新的资本集聚地,比如芒果TV在2019年就发起了致力于打造芒系中短视频内容矩阵的“大芒计划”,2021年优酷先后发布了“扶摇计划”和“好故事计划”两大内容招募活动,同年B站联合多家影视机构、头部UP主,打造展示单集3-10分钟微短剧的“轻剧场”;第三层面,当网络微短剧生产热火朝天,已经被纳入广电行政部门政策监管时,竖屏微短剧作为标签产品开始为资本所助力推进。如2019年快手宣布上线“快手小剧场”,2021年10月快手“星芒计划”正式升级为“星芒短剧”;2021年抖音才正式上线“短剧新番计划”,今年6月就整合升级为“剧有引力计划”;两大超级短视频平台的扶持重心均主要在竖屏微短剧——竖屏是这两个平台有别于其他传统流媒体平台的最显著标识。可以预想的是,资本的持续注入一定会改变当下竖屏微短剧仍主要为专业化用户(UPGC)自发生产的生态,当精品剧、现象剧不断涌现并成为创作标杆时,或许竖屏微短剧的形态特征就有可能重新被定义。
不过归根结底,竖屏微短剧的风行原因在于大众接受影像信息的情感逻辑。张爱玲在《多少恨》中谈及电影时曾经说过,“现代的电影院本是最大众化的王宫”。她的“王宫”比喻指向电影“造梦”的机制——影像可以短暂地满足人们的情感需求,或者说,影像故事就是人们的白日梦。这一机制同样适用于竖屏微短剧,仔细观察各种类型的竖屏微短剧,单集中通常都会有情节的节点,而这些被称为“爆点”“笑点”“泪点”“燃点”的节点都与人们的情感紧密相关。在短暂观剧的碎片时间段里,人们虽然无法像观影或追剧那样获得沉浸式的体验,但瞬间的情感碰撞或释放同样是他们所需要的——尤其是在加速社会的压力之下。以在抖音拥有1400万粉丝的短剧《食堂夜话》为例,该剧的结构方式似乎移植自经典电视剧IP《深夜食堂》,每两集讲述一个打动人的爱情小故事。问题在于,仅仅靠影像与人物台词,一两分钟时间内很难表现一个完整故事。于是,创作者让料理店的老板/男主人化身为故事的讲述人,既补充故事信息,也推动剧情前进。有意思的是,故事节奏当然很快,但讲述人的语气却是娓娓道来,并且时不时地发表抒情感慨,他告诉你“朝暮与年岁并往,我与你一同行至天光”,告诉你“世上最好的治愈方式,是体谅和耐心”,告诉你“平淡不是终点,平凡的陪伴才是长久”。这些话语仿佛情感的细雨点点滴滴,呼唤着观众们的心灵共鸣。
竖屏微短剧的受众主体是年轻人,由大多数作品中女主角绝对突出的戏份及表现也可以看出,青年女性更是竖屏微短剧的主力受众。在无数年轻人与无数微短剧共鸣互动、一起编织的“白日梦”中,实际上沉淀着属于一个时代的年轻人的感觉结构(Feeling Structure)。诚如威廉斯所说, “……但新的一代人将会有他们自己的感觉结构,这种感觉结构看起来不像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因为在这里,最明显不过的是,变化中的组织就好比是一个有机体: 新的一代以自己的方式对它所继承的那个独一无二的世界作出反应,在很多方面保持了连续性,同时又对组织进行多方面的改造,最终以某些不同的方式来感受整个生活,把自己的创造性反应塑造成一种新的感觉结构。”在这个意义上,竖屏微短剧不仅是生机盎然的娱乐样本,也是意味深长的社会心理样本。
需要指出的是,竖屏微短剧生产的情感逻辑也从未脱离过商业逻辑。即便像抖音、快手那样宣称“记录美好生活”或者“记录世界记录你”,其实它们遵循的依然是情感经济学的法则,亨利·詹金斯认为,“情感经济”是影响消费者决策行为的新方式,“最有价值的消费者是那些业内称之为忠诚者的人,或者说是我们称之为粉丝的人。忠诚者更倾向于忠实地收看,更倾向于注意广告和购买产品。”当某一部竖屏微短剧积累到足够的粉丝时,就获得了相应的可以变现的流量。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是,顶流的竖屏剧作品在剧集中会有相当多的广告植入。较之于电视剧中相对隐性的广告植入,竖屏剧的广告植入显得直截了当,大多数商品是洗发水、护肤膏、饮用水等百姓日用消费品。有些情况下,竖屏剧单集剧情甚至直接为商品量身定制,配合竖屏下方即看即买或是转场直播间的链接,一集集的短剧就像商品展示的橱窗,形成了不断提供营销机会的影像生产流水线。只不过,这条流水线上生产的不仅是属于消费者的大众的梦,也生产着属于创业者的小众的梦。
*为方便电子阅读,已略去原文注释,如需完整版本,请查阅首发纸刊。

作者:刘永昶,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